
衛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達銅像考
──兼述咱雅班第達生平
羅文華
故宮博物院院刊
1997年第一期(1997.02)
頁82-85
©1997 紫禁城出版社
中國 北京
| 頁82 | 衛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達銅像考--兼述咱雅班第達生平 |
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02) |
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佛像藏品中,有一尊祖師像極為引人注目(圖版四)。此像高34厘米,為紅銅片拍打而成,外表鎏金。袓師右手施說法印,左手施襌定印,跏趺坐于三層座墊之上,面容清癯,皺紋滿布,慈顏含笑,雙耳直立,一副飽經滄桑但意志堅定的睿智老者形象。肥大的袈裟裹住全身,下襬垂落于座墊之上,線條流暢生動。從其面部表情的栩栩如生以及內在氣質的強烈感染力上可以找到15世紀以來典型的西藏風格祖師像模式,但是從一些工藝特點,如用銅片拍打成型,鎏金明亮,線條準確自如以及一些表現手法,如鼻梁修直、鼻尖略勾等方面看,它與蒙占咱那巴扎爾(Zanabazar)時期的作品[1]。風格接近,都具有尼泊爾藝術的特點。因此,此像的成造年代應該在17世紀。
袓師像座底板中心刻劃的是十字交杵圖案,兩邊各起數行托忒文題記(圖一),字體大小不一,書寫也不很規範,想完全準確地辨識出來有很大的困難,雖經反復核對,仍有部分詞句不甚通順。現將原文轉寫如下[2](有疑問處用“?”標明):
Sedkeletenchi Iamatani gegen boskhoghson mini budan yēr ecestü ghurban mini Zayātan yoson bolōdtai (?) shajini baruldan töröji dēre ügei badochin(?) khutughtu(r) ötöreulkhu boltoghai.
原文大意為:
“在水曜日,如願喇嘛佛像終于塑造出來了,完成了三尊之一咱雅的佛像,呼喚呼圖克圖的轉世照這個佛像立即出現。”
雖然。我們無法查對題記中提到的“水曜日”所指的確切日期,但可以肯定這是一尊咱雅班第達的銅像,並且是在他圓寂後不久塑造的。成造的目的是為了表達對咱雅班第達的哀思之情並祈求新的靈童盡快轉世。
| 頁83 | 衛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達銅像考--兼述咱雅班第達生平 |
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02) |
咱雅班第達是衛拉持蒙古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人物之一,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蒙古諸部形成了漠南、漠北、漠西三足鼎立的態勢。咱雅班第達是漠西蒙古衛拉特四部中最著名的活佛(呼圖克圖)[3],他對蒙古族的政冶穩定、經濟發展以及文化繁榮所作的貢獻是同時期的其他活佛所無法比肩的。但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有關咱雅班第達生平事蹟的記載卻寥若辰星,目前最詳實的文獻應屬咱雅班第達的弟子拉德納巴德拉于17世紀末用托忒文撰寫的《咱雅班第達傳》。此傳記己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成崇德副教授譯成漢文[4]。通過這部傳記,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他一生的主要事蹟及此像成造的緣起,從而準確地推斷出此像成造的時間。

圖一 咱雅班第達像底板上的托忒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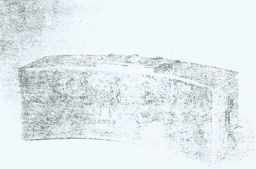
圖二 噶爾丹銀經筒
咱雅班第達(1599-1662年),原名南喀嘉措(Nam-mkhahi-rgya-mtsho),出生於衛拉特蒙古和碩特部的望族桑噶斯(Sangkhas)家族。
17世紀初,藏傳佛教格魯派(也稱黃教)開始影響到衛拉特蒙古。1615年(明萬曆四十三年),曼殊室利呼圖克圖以達賴喇嘛代表的身份來到衛拉特蒙古,勸說當時作為衛拉特四部聯盟丘爾干的領袖、和碩特部的首領拜巴噶斯皈依黃教。拜巴噶斯受其感化,欣然下令讓自已年滿16歲的義子咱雅班第達替自己出家,同時命其他王公貴族各派一名年輕子弟當喇嘛。次年,咱雅班第達動身前往西藏的拉薩學習佛法。在拉薩期間,由於他學習勤奮,加之天資聰穎,很快精通了顯、密教法,獲得最高學位--拉讓巴格西,並有幸成為五世達賴喇嘛身邊的十大比丘之一,先後得到吉本(或哲布尊)和阿巴兩個法位。同時,他與藏南扎什倫布寺的四世班禪也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經過長達22年的學佛生活之後,諳熟經典、飽學多識、己年近四旬的咱雅班第達肩負著在衛拉特蒙古進一步推廣黃教、密切衛拉特蒙古諸部與黃教間良好關係的雙重任務躊躇滿志地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
從1639年(清崇德四年)始,到1662年(清康熙元年)咱雅班第達圓寂於去西藏的路上為止的23年中,他先後向東傳法到喀爾喀蒙古的扎薩克圖、土謝圖、車臣等部,向西遠及伏爾加河下游的土爾扈特部,為王公貴族和平民百姓誦經、祈褔、主持葬禮、舉辦法事,使黃教在衛拉特蒙古和喀爾喀蒙古地區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也為自己嬴得了很高的地位,深受蒙古族社會各階層的尊敬。
在宣傳佛法的同時,他也為衛拉特蒙古族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1644年(清順治元年),他著手翻譯了著名的藏族文獻《瑪尼全集》。隨著蒙、藏民族文化交流的日趨活絡以及佛經翻譯的需
| 頁84 | 衛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達銅像考--兼述咱雅班第達生平 |
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02) |
要,1648年(順治五年),他在回鶻式蒙文的基礎上針對衛拉持蒙古方言的特點。創制了衛拉特民族自己的規範性文字──托忒文(“托忒”原意是“清楚”、“明瞭”的意思,是對這種文字的贊美之詞,又稱衛拉特文)。這樣文字接近口語,能清楚地表達衛拉特方言,在溝通蒙、藏文化,保存衛拉特民族歷史文獻方面具有顯著作用,迄今仍為我國新疆地區蒙古族所通用。此後,咱雅班第達利用這種文字翻譯了170餘部藏文文獻,其中包括佛典、倫理、歷史、文學、醫學等多方面著作,並記錄下衛拉特蒙古著名的英雄史詩《江格爾》,推動了衛拉特蒙古族文化的發展。
在他去西藏留學期間,衛拉特蒙古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嚴峻局面。為了共同抵禦沙俄侵略努力日趨加劇的威脅,停止與喀爾喀蒙古的長期戰爭,消除內部諸部落間經常性的紛爭和分裂,在準噶爾部首領巴圖爾琿台吉的倡導下,於塔爾巴哈台召開了由衛拉特蒙古和喀爾喀蒙古各部參加的王公會議。剛從西藏回來不久的咱雅班第達積極參加了這次盛會。會議簽署了著名的《1640蒙古衛拉特法典》,使衛拉特蒙古和喀爾喀蒙古結成了新的更廣泛的同盟。這部法典還明確宣布藏傳佛教是蒙古族各部的共同信仰。
為了貫徹《法典》和會議精神,咱雅班第達還利用自已在衛拉特蒙古以及喀爾喀蒙古中的影響積極奔走,為協調各部落的關係,促進衛拉特蒙古內部的穩定、減少內外戰爭的消耗而努力。他先後調解了兩次重大的衝突:一次是巴圖爾琿台吉與和碩特部的昆都侖鳥巴什之間的武裝衝突(1646-1647年);一次是巴圖爾琿台吉病逝之後,其子僧格與兄弟之間為爭奪汗位而起的戰爭。可以說,正是由於他個人的突出貢獻,才使得衛拉特蒙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著相對的穩定和發展。
同時,他還對剛剛入關逐鹿中原的清王朝表現出非常友好的態度。據《清實錄》記載,順冶四年(1647年)十一月,咱雅班第達曾親自到北京覲見順治帝,並在太和殿接受賜宴[5]。時隔不久,在五世達賴喇嘛受清王朝邀請去北京的路上,咱雅班第達請求達賴喇嘛向清帝進言,望清帝幫助傳播蒙古文字和佛典,反映出他敏銳的政冶眼光以及對清政府的信賴和期望。
可以這樣說,咱雅班第達在衛拉特歷史上同時扮演著宗教家、學者、政治家三重角色,在復雜變幻的歷史風雲中,他為本民族的生存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咱雅班第達圓寂之後,在拉薩舉行了隆重的葬禮。1663年夏,遵照達賴喇嘛的指示,由莫尼達爾瑪、阿木幸、咱塔那等16位尼泊爾工匠分別成造密集金剛(Guhayasamaja)、大威德金剛(Yamantaka)、彌勒佛(Maitreya)和咱雅班第達像。兩個月之後順利完工。咱雅班第達像先在達賴喇嘛身邊存放三天後,由其弟子們帶回衛拉特蒙古,供人們瞻仰禮拜。
故宮博物院保存的這尊咱雅班第達像極有可能就是1663年夏由尼泊爾工匠成造的那一尊。如前文所提,此像具有尼泊爾風格,鑄造年代應在17世紀,與《咱雅班第達傳》中所提及的成造年代(17世紀70年代)一致。像從面部看是一老者形象,應是咱雅班第達圓寂前面容的寫真。《咱雅班第達傳》中還提到咱雅班第達像高1尺,當時蒙古的1尺與此像的實測高度(34厘米)相當。從現在發表的實物資料看,這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的唯一的一尊咱雅班第達塑像,也是最早的一件與衛拉特蒙古有關的藝術品。
由於銅像上沒有發現入宮時繫的黃條,也沒有佛龕,無法找到此像進入宮中的直接材料,但是根據宮中現存佛像的來源,結合衛拉特蒙古的歷史背景,筆者認為主要有三種可能性:
1. 此像可能是作為蒙古貴族或喇嘛的貢品送入宮中的。從乾隆十八年(1753年)開始。清政府在衛拉特蒙古逐漸實行設旗
| 頁85 | 衛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達銅像考--兼述咱雅班第達生平 |
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02) |
制度,並規定“蒙藏喇嘛均遵清廷勅旨,按年或分班遣使入貢,遇大慶典。例須特貢。”“貢品有哈達、佛像、馬匹,不定以額。”[6]
2. 在當時頻繁的戰爭中,一些珍貴的藏傳佛教法器、佛像被當作戰利品呈進宮中,此像可能是其中之一。從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初,衛拉特四部聯盟的領袖一直是由和碩特部的首領擔任,到17世紀30年代,準噶爾部崛起,取代了和碩特部的地位,在此後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因與清王朝的統一政策發生激烈衝突,戰爭不斷。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噶爾丹(1644-1697年)在烏蘭布通遭清軍重創。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昭莫多戰役,清軍全殲噶爾丹主力,噶爾丹病逝。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1688-1727年)進軍西藏。在清軍的干涉下也遭敗績。其子噶爾丹策零(1727-1745年)于1731年(雍正九年)與清軍在額爾德尼召會戰中,準噶爾部受到沉重打擊,損失嚴重。此後,清軍又平定了達瓦齊(1755年,乾隆二十年)和阿睦爾撒納(1756-1757年,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的叛亂。現故宮歷代藝術館中長期陳列著一件銀制的經筒(圖二),就是清軍在與噶爾丹的戰爭中繳獲的。
3. 可能先由衛拉特蒙古貴族或喇嘛獻到西藏寺中,後由西藏貢進北京;衛拉特蒙古在17世紀30-40年代就已控制了青海和西藏。由於黃教在衛拉特蒙古獲得了眾多虔誠的信徒,各部貴族與西藏的大喇嘛及寺院往來頻繁,他們經常親率部眾或派人到西藏熬茶,布施,供奉財物。
總之,咱雅班第達是衛拉特蒙古族歷史中最傑出的一人,他在維護民族團結、發展民族文化等方面貢獻頗巨,迄今在新疆地區的蒙古族人們的心中仍占有很高的地位,此造像的發現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衛拉特蒙古族人民中都將引起廣泛的關注。
清史所副所長成崇德副教授在百忙之中為本文的撰寫與修改提出不少寶貴意見,筆者謹此致謝。
1. 見 The Eminent Mongolian Sculptor--G. Zanabazar,烏蘭巴托國家出版社,1982年。
2. 題記原文經清史所副所長成崇德副教授及新疆政協主席巴岱先生辨認、抄寫,並由成先生譯成漢文。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奧其爾老師將其轉寫出來。
3. 王輔仁、陳慶英編著《蒙藏民族關係史略》第8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10月。
4. 《中國邊疆史地資料叢刊.蒙古卷.清代蒙古高僧傳譯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制中心出版,1991年1月。
5. 《清實錄》三“世袓實錄”卷三十五,中華書局,1985年8月。“順治四年十一月……丁己,上御太和殿賜厄魯特部落喇木占霸胡土克圖、單儲特霸達爾漢綽爾濟、喀爾喀部落扎薩克圖汗下額爾克溫布及土謝圖汗下杜爾伯等宴。”文中的“喇木占霸胡土克圖”即指咱雅班第達。
6. 妙丹法師編《蒙藏佛教史》(下)第六篇“清代之喇嘛”,上海佛學書局,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
(責任編輯:張 露)
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铜像考
──兼述咱雅班第达生平
罗文华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97年第一期(1997.02)
页82-85
©1997 紫禁城出版社
中国 北京
| 页82 | 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铜像考--兼述咱雅班第达生平 |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02) |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佛像藏品中,有一尊祖师像极为引人注目(图版四)。此像高34厘米,为红铜片拍打而成,外表鎏金。袓师右手施说法印,左手施禅定印,跏趺坐于三层座垫之上,面容清癯,皱纹满布,慈颜含笑,双耳直立,一副饱经沧桑但意志坚定的睿智老者形象。肥大的袈裟裹住全身,下摆垂落于座垫之上,线条流畅生动。从其面部表情的栩栩如生以及内在气质的强烈感染力上可以找到15世纪以来典型的西藏风格祖师像模式,但是从一些工艺特点,如用铜片拍打成型,鎏金明亮,线条准确自如以及一些表现手法,如鼻梁修直、鼻尖略勾等方面看,它与蒙占咱那巴扎尔(Zanabazar)时期的作品[1]。风格接近,都具有尼泊尔艺术的特点。因此,此像的成造年代应该在17世纪。
袓师像座底板中心刻划的是十字交杵图案,两边各起数行托忒文题记(图一),字体大小不一,书写也不很规范,想完全准确地辨识出来有很大的困难,虽经反复核对,仍有部分词句不甚通顺。现将原文转写如下[2](有疑问处用“?”标明):
Sedkeletenchi Iamatani gegen boskhoghson mini budan yēr ecestü ghurban mini Zayātan yoson bolōdtai (?) shajini baruldan töröji dēre ügei badochin(?) khutughtu(r) ötöreulkhu boltoghai.
原文大意为:
“在水曜日,如愿喇嘛佛像终于塑造出来了,完成了三尊之一咱雅的佛像,呼唤呼图克图的转世照这个佛像立即出现。”
虽然。我们无法查对题记中提到的“水曜日”所指的确切日期,但可以肯定这是一尊咱雅班第达的铜像,并且是在他圆寂后不久塑造的。成造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对咱雅班第达的哀思之情并祈求新的灵童尽快转世。
| 页83 | 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铜像考--兼述咱雅班第达生平 |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02) |
咱雅班第达是卫拉持蒙古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之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蒙古诸部形成了漠南、漠北、漠西三足鼎立的态势。咱雅班第达是漠西蒙古卫拉特四部中最著名的活佛(呼图克图)[3],他对蒙古族的政冶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繁荣所作的贡献是同时期的其它活佛所无法比肩的。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咱雅班第达生平事迹的记载却寥若辰星,目前最详实的文献应属咱雅班第达的弟子拉德纳巴德拉于17世纪末用托忒文撰写的《咱雅班第达传》。此传记己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成崇德副教授译成汉文[4]。通过这部传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他一生的主要事迹及此像成造的缘起,从而准确地推断出此像成造的时间。

图一 咱雅班第达像底板上的托忒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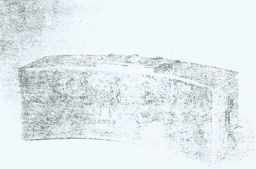
图二 噶尔丹银经筒
咱雅班第达(1599-1662年),原名南喀嘉措(Nam-mkhahi-rgya-mtsho),出生于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的望族桑噶斯(Sangkhas)家族。
17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也称黄教)开始影响到卫拉特蒙古。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曼殊室利呼图克图以达赖喇嘛代表的身份来到卫拉特蒙古,劝说当时作为卫拉特四部联盟丘尔干的领袖、和硕特部的首领拜巴噶斯皈依黄教。拜巴噶斯受其感化,欣然下令让自已年满16岁的义子咱雅班第达替自己出家,同时命其它王公贵族各派一名年轻子弟当喇嘛。次年,咱雅班第达动身前往西藏的拉萨学习佛法。在拉萨期间,由于他学习勤奋,加之天资聪颖,很快精通了显、密教法,获得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并有幸成为五世达赖喇嘛身边的十大比丘之一,先后得到吉本(或哲布尊)和阿巴两个法位。同时,他与藏南扎什伦布寺的四世班禅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过长达22年的学佛生活之后,谙熟经典、饱学多识、己年近四旬的咱雅班第达肩负着在卫拉特蒙古进一步推广黄教、密切卫拉特蒙古诸部与黄教间良好关系的双重任务踌躇满志地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
从1639年(清崇德四年)始,到1662年(清康熙元年)咱雅班第达圆寂于去西藏的路上为止的23年中,他先后向东传法到喀尔喀蒙古的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部,向西远及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为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诵经、祈褔、主持葬礼、举办法事,使黄教在卫拉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也为自己嬴得了很高的地位,深受蒙古族社会各阶层的尊敬。
在宣传佛法的同时,他也为卫拉特蒙古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644年(清顺治元年),他着手翻译了著名的藏族文献《玛尼全集》。随着蒙、藏民族文化交流的日趋活络以及佛经翻译的需
| 页84 | 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铜像考--兼述咱雅班第达生平 |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02) |
要,1648年(顺治五年),他在回鹘式蒙文的基础上针对卫拉持蒙古方言的特点。创制了卫拉特民族自己的规范性文字──托忒文(“托忒”原意是“清楚”、“明了”的意思,是对这种文字的赞美之词,又称卫拉特文)。这样文字接近口语,能清楚地表达卫拉特方言,在沟通蒙、藏文化,保存卫拉特民族历史文献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迄今仍为我国新疆地区蒙古族所通用。此后,咱雅班第达利用这种文字翻译了170余部藏文文献,其中包括佛典、伦理、历史、文学、医学等多方面著作,并记录下卫拉特蒙古著名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推动了卫拉特蒙古族文化的发展。
在他去西藏留学期间,卫拉特蒙古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为了共同抵御沙俄侵略努力日趋加剧的威胁,停止与喀尔喀蒙古的长期战争,消除内部诸部落间经常性的纷争和分裂,在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倡导下,于塔尔巴哈台召开了由卫拉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各部参加的王公会议。刚从西藏回来不久的咱雅班第达积极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签署了著名的《1640蒙古卫拉特法典》,使卫拉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结成了新的更广泛的同盟。这部法典还明确宣布藏传佛教是蒙古族各部的共同信仰。
为了贯彻《法典》和会议精神,咱雅班第达还利用自已在卫拉特蒙古以及喀尔喀蒙古中的影响积极奔走,为协调各部落的关系,促进卫拉特蒙古内部的稳定、减少内外战争的消耗而努力。他先后调解了两次重大的冲突:一次是巴图尔珲台吉与和硕特部的昆都仑鸟巴什之间的武装冲突(1646-1647年);一次是巴图尔珲台吉病逝之后,其子僧格与兄弟之间为争夺汗位而起的战争。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个人的突出贡献,才使得卫拉特蒙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发展。
同时,他还对刚刚入关逐鹿中原的清王朝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据《清实录》记载,顺冶四年(1647年)十一月,咱雅班第达曾亲自到北京觐见顺治帝,并在太和殿接受赐宴[5]。时隔不久,在五世达赖喇嘛受清王朝邀请去北京的路上,咱雅班第达请求达赖喇嘛向清帝进言,望清帝帮助传播蒙古文字和佛典,反映出他敏锐的政冶眼光以及对清政府的信赖和期望。
可以这样说,咱雅班第达在卫拉特历史上同时扮演着宗教家、学者、政治家三重角色,在复杂变幻的历史风云中,他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咱雅班第达圆寂之后,在拉萨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663年夏,遵照达赖喇嘛的指示,由莫尼达尔玛、阿木幸、咱塔那等16位尼泊尔工匠分别成造密集金刚(Guhayasamaja)、大威德金刚(Yamantaka)、弥勒佛(Maitreya)和咱雅班第达像。两个月之后顺利完工。咱雅班第达像先在达赖喇嘛身边存放三天后,由其弟子们带回卫拉特蒙古,供人们瞻仰礼拜。
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这尊咱雅班第达像极有可能就是1663年夏由尼泊尔工匠成造的那一尊。如前文所提,此像具有尼泊尔风格,铸造年代应在17世纪,与《咱雅班第达传》中所提及的成造年代(17世纪70年代)一致。像从面部看是一老者形象,应是咱雅班第达圆寂前面容的写真。《咱雅班第达传》中还提到咱雅班第达像高1尺,当时蒙古的1尺与此像的实测高度(34厘米)相当。从现在发表的实物资料看,这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的唯一的一尊咱雅班第达塑像,也是最早的一件与卫拉特蒙古有关的艺术品。
由于铜像上没有发现入宫时系的黄条,也没有佛龛,无法找到此像进入宫中的直接材料,但是根据宫中现存佛像的来源,结合卫拉特蒙古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性:
1. 此像可能是作为蒙古贵族或喇嘛的贡品送入宫中的。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开始。清政府在卫拉特蒙古逐渐实行设旗
| 页85 | 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铜像考--兼述咱雅班第达生平 |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02) |
制度,并规定“蒙藏喇嘛均遵清廷勅旨,按年或分班遣使入贡,遇大庆典。例须特贡。”“贡品有哈达、佛像、马匹,不定以额。”[6]
2. 在当时频繁的战争中,一些珍贵的藏传佛教法器、佛像被当作战利品呈进宫中,此像可能是其中之一。从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卫拉特四部联盟的领袖一直是由和硕特部的首领担任,到17世纪30年代,准噶尔部崛起,取代了和硕特部的地位,在此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因与清王朝的统一政策发生激烈冲突,战争不断。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1644-1697年)在乌兰布通遭清军重创。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昭莫多战役,清军全歼噶尔丹主力,噶尔丹病逝。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1688-1727年)进军西藏。在清军的干涉下也遭败绩。其子噶尔丹策零(1727-1745年)于1731年(雍正九年)与清军在额尔德尼召会战中,准噶尔部受到沉重打击,损失严重。此后,清军又平定了达瓦齐(1755年,乾隆二十年)和阿睦尔撒纳(1756-1757年,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的叛乱。现故宫历代艺术馆中长期陈列着一件银制的经筒(图二),就是清军在与噶尔丹的战争中缴获的。
3. 可能先由卫拉特蒙古贵族或喇嘛献到西藏寺中,后由西藏贡进北京;卫拉特蒙古在17世纪30-40年代就已控制了青海和西藏。由于黄教在卫拉特蒙古获得了众多虔诚的信徒,各部贵族与西藏的大喇嘛及寺院往来频繁,他们经常亲率部众或派人到西藏熬茶,布施,供奉财物。
总之,咱雅班第达是卫拉特蒙古族历史中最杰出的一人,他在维护民族团结、发展民族文化等方面贡献颇巨,迄今在新疆地区的蒙古族人们的心中仍占有很高的地位,此造像的发现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卫拉特蒙古族人民中都将引起广泛的关注。
清史所副所长成崇德副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文的撰写与修改提出不少宝贵意见,笔者谨此致谢。
1. 见 The Eminent Mongolian Sculptor--G. Zanabazar,乌兰巴托国家出版社,1982年。
2. 题记原文经清史所副所长成崇德副教授及新疆政协主席巴岱先生辨认、抄写,并由成先生译成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奥其尔老师将其转写出来。
3. 王辅仁、陈庆英编着《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第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0月。
4. 《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蒙古卷.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1年1月。
5. 《清实录》三“世袓实录”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8月。“顺治四年十一月……丁己,上御太和殿赐厄鲁特部落喇木占霸胡土克图、单储特霸达尔汉绰尔济、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下额尔克温布及土谢图汗下杜尔伯等宴。”文中的“喇木占霸胡土克图”即指咱雅班第达。
6. 妙丹法师编《蒙藏佛教史》(下)第六篇“清代之喇嘛”,上海佛学书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责任编辑:张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