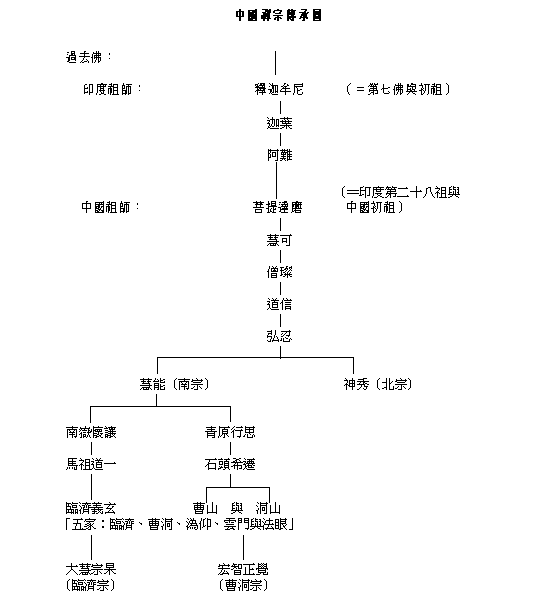
審視傳承──陳述禪宗的另一種方式
印第安納大學副教授 馬克瑞
中華佛學學報
第13期(2000)
頁281-298

頁281
提要
論章的目的是討論「我們應該如何審視禪宗?」的問題,立場是主張該用多元的觀點與變遷不定的分析性類型研究。如果這樣,我們不斷地繼續努力避免傳統性看法、來自資料本身的結構上限制。所謂「傳統性看法」表示禪宗傳承圖所含有的意思,因為它有解釋與溝通的媒介所具的語言符號的效用。
第一、禪宗的傳承體系是印度和中國文化結合的產物,可就不用現在學者們經常把禪宗描述成所有中國佛教禪宗派中「最中國的」的空洞沙文主義說法。
第二、用此傳承圖把禪宗定義為「教外別傳」,藉此宣稱禪宗在根本上勝過其他一切宗派,有挑起爭議的暗示。
第三、在禪宗傳承體系中具有意義的不是發生在釋迦牟尼、菩提達摩、慧能和其他人身上的「事實」,而是這些人物在禪宗的神話裡如何被看待。最重要的是軼事經由什麼過程而被創作、流傳、編輯與修訂,因而傳遍禪宗修行人與支持者全體,直到此軼事成為具可塑性的傳說傳統。這是馬克瑞的禪宗研究第一定律:「它不是事實,因此更加重要!」
第四、根據有關空性的說理,在此傳承體系中沒有任何事物是真正被傳承下來的,發生在每位大師與他的繼承者之間的,只是對繼承者達到完全開悟的印可。
第五、由於每位佛陀與祖師的開悟都是徹底的,在印度的諸佛與祖師以及在中國與其相當的人物,彼此間並無宗教地位的差別。從佛教的中國化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六、禪的「系譜模式」之所以重要,不僅作歷史上的自我認識;同樣重要的是它解釋了禪宗修行的方式,則暗示最重要的心靈培育,是在於師徒之間的「應對」(encounter)。
第七、我提到「每位大師與他的(男性)繼承者」,這個指稱特定性別的措詞非常適合此處。禪宗傳統是極為以男性為主的,英文「patriachal」(指禪宗代表性人物或男性中心的思想體系)一詞的模稜兩可中全適合此處了。雖然現在無法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很敏感地觀察到:禪不只是開發新的宗教可能性的工具,卻也是壓制一般中國宗教修行人或其中的不同團體的武器嗎?
每當我們根據大師代代相傳的直線繼承關係,來對禪宗作出解釋的時候,我們是在冒著犯下我所說的「念珠」式謬見的險。這是誤報比此謬見模式更複雜而且更有意思的歷史、宗教的狀況。1
關鍵詞:1.傳承 2.宗派 3. 系譜 4.機緣問答 5.大師
頁283
我應該怎樣開始這個關於禪宗的討論?
許多作者選擇的方式,是從一些能激發好奇心、有趣的軼聞故事作為開始。在禪宗典籍裡的確有許多這樣的好例子,像是一位中年僧人──後來的二祖慧可──為了向菩提達磨求法而自斷手臂。為了激勵初學者精進,這個故事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禪堂(僧堂)已被講了不知多少遍!或者我可以找個較不恐怖的像龐居士的故事:他因為體悟了追逐世俗財富之無益而把家財擲於江中。這個無罣礙的自發性的例子想必是用來傳達給我們某種深刻的精神上的啟示吧?這些涵意略有不同的傳奇記載幾乎是取之不竭的。當然還有其他可能的開頭。我也可以選擇一個適宜的方式來描述禪宗的最基本特徵,亦即能概括整個禪宗傳統的一些特點或一系列特徵。或者我可以避免這種貧乏的概括化,而頌揚禪宗傳統在數世紀間驚人的創造力、其作為宗教現象所具的活力。
儘管我如此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我卻已作好了選擇,亦即要以發問作為開頭,不只用以激發你們的好奇心,還要激發你們的批判能力。我特別要問:我們應該如何審視禪宗?我們應採取什麼方法,避免什麼方法?什麼樣的分析會是有效的,而什麼樣的只是重複普遍被接受的刻板印象?
「我們應該如何審視禪宗?」是我們不能也不應迴避的問題;完全忽略此問題,一開始就詳述某些事件和觀念,其實是事先已對此問題作出判決,而不去承認它的重要性。但是以斷然而簡單的言詞來陳述答案也不妥當:當我在二十世紀末的臺北近郊撰寫此文之時,我意識到在這個講解過程中──我個人和我的聽眾之中──隱含著文化特性所具的驚人的多元價值。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時間,我是個學者與修行人、學生與老師、愛戀者與遁世者,而且我透過在美國、日本和臺灣的一連串廣泛的教育方面的機緣學習到現在正要發表的東西。本文不只要給中國的聽眾和讀者使用,也要給西班牙、美國、日本的聽眾和讀者使用,所以我怎能假定應該只有一種審視禪宗的方式?在這個後現代(post-modern)的世界裡,多元的觀點與變遷不定的分析性類型研究已經是既成的事實了。
一、解構(deconstruct)禪宗傳承圖
為了方便起見,讓我先釐清我想要解構並從而避免的對禪宗的觀點。或許我最好承認我只是想諷刺這個觀點,以便以下的評論能成為一支杠桿,藉以讓我們推進到某種見解中(改寫杜威和胡適所說的,研究過去以創造出一種杠桿,藉此把中國推進到某種未來)。我所指的觀點是以下一頁的傳承圖來描述的傳統主義的方法。幾乎每一本有關禪宗的書都有像這樣的圖;我首先要做的不是思考此圖本身的內容,而是注意它作為解釋與溝通的媒介所具的語言符號的效用。如果媒介就是訊息,此圖本身的構造傳達了什麼訊息?
頁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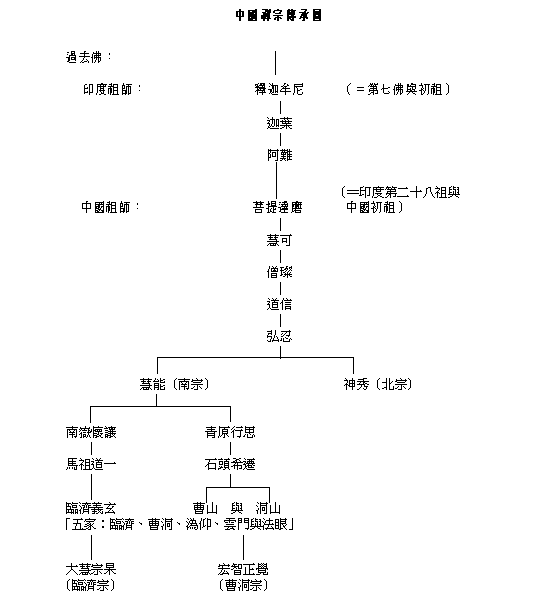
禪宗經常被稱作「不立文字」並代表「教外別傳」。人們幾乎總是──如我正要做的──以「禪宗的確使用許多文字來表達其教義」的諷刺評論來介紹這些語詞。後面我們會回來看禪宗對語言的使用以及其不「立」文字,但是現在我們可以注意到,傳承圖為禪宗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背景提供了基本的模式。那就是,禪宗不把自己定義為依據特定典籍的佛教宗派(school)2 (就像天台宗重《法華經》),而是定義
頁285
為佛教本身,或佛教唯一的中心教義,它由過去七佛傳到十八位印度祖師、六位中國祖師,乃至其後所有世代的中國、韓國和日本的禪宗大師。(注意:釋迦牟尼,即我們通常認為的「歷史上的」佛陀──禪宗對之有其獨特的看法──既是過去七佛的最後一位,也是印度祖師中的第一位。同樣地,菩提達磨是印度第二十八祖與中國初祖。)這整個圖歷經好幾世紀才發展出來;最早的基本要素出現於第七世紀末,完整的體系也許早在801年即已流通,但可確定在952年以前已經流通。
一開始便考慮此傳承圖的好處之一當然是它介紹了我們的故事中若干最重要的角色。過去七佛是傳說的人物,我們只需稍加留意;雖然禪宗典籍略為鋪陳並修飾這七佛的宗教身分,但就我們的目的而言,我們可以承認他們僅僅可當作禪宗繼承了東亞大乘佛教大傳統之一部份的證據。我們也不必太留意二十八位印度祖師。他們的傳記是以什麼方式撰述的,是個有趣、但太複雜的研究課題,我們在此沒有篇幅可供討論。3 另一方面,從菩提達磨以來的六位中國祖師,加上第六代的慧能與神秀,以及他們之後好幾代的弟子,將會比其他角色更常出現在這齣戲。(讀者會立刻注意到在我們的傳承圖中沒有任何一位神秀的弟子,這是此圖本身明顯的刪除。在頁291我將對此作簡短的評論。)被紀念為臨濟宗和曹洞宗的聖像的那些人物的名字構成此圖的其餘部分,他們可列入禪宗傳統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
我們可以由此傳承圖得到一些重要而基本的推論。
第一、歷史起源的暗示:禪宗的傳承體系是印度和中國文化結合的產物。現在學者們經常把禪宗描述成所有中國佛教宗派中「最中國的」,他們部分是指禪宗的系譜(genealogical)模式。(實際上我特別不喜歡這種表達,因為這種表達不過是由文化的沙文主義觀念所產生的未經闡釋的套言,而非分析的洞見。鈴木大拙和其他人就日本禪宗也表達了幾乎相同的看法,亦即它在某種角度上呈現出日本的文化的本質。此事應提醒我們注意這種意見中本質上的空洞與策略上的意圖。) 實際上,這個傳承體系的起源可見於印度佛教以及第四、第五世紀罽賓(喀什米爾)的佛教禪修傳統,我們以後會在這些演講中看見。禪宗傳承體系與第八世紀及其後的中國家族系譜有一些相似點;但是我們應記得,印度佛教徒就像中國人一樣有父母、師長、家族系譜和師徒傳承。4 雖然中國禪宗傳承圖是由印度和中國的元素構成的混合物,但它是在中國佛教的環境中發展而成,而且特別能適應此環境。我們可以改寫鄧小平的話,把它稱作「具有中國特色的禪宗系譜理論」。5
第二、禪宗的唱導者用此傳承圖把禪宗定義為「教外別傳」,藉此宣稱禪宗迥異於其他一切宗派,並且在根本上勝過其他一切宗派。其他宗派只陳述對佛教的種種解釋,而禪宗則陳述了真正的佛教本身。禪宗跨出了這個容易挑起爭議的一步,用以建立在所有宗派中的優越性。其他東亞佛教宗派的反應則是去設計屬於自己的傳承體系,或者說禪宗只強調戒、定、慧「三學」之一,因此只陳述了佛教的一個構成要素而已。無論我們是把中古時代的中國佛教徒視為只關心最高智慧,或汲汲於獲得皇室贊助與其世俗利益,至少他們是在與同時代的人角逐知識與文化上的領導權。我們不應輕忽傳承理論具有能挑起爭議的特質。
第三、在禪宗傳承體系中具有意義的不是發生在釋迦牟尼、菩提達磨、慧能和其他人身上的「事實」,而是這些人物在禪宗的神話裡如何被看待。這個論點會在此不斷出現,而且我要提出底下這個複雜的主張:在一次又一次的案例中,根據一種簡單地評斷新聞精確性的標準來看,在典籍中說有發生的,幾乎一定不曾發生。但我們應注意的是涉及神話創作過程的動力,而非執著於事實與捏造的概念。任何軼事是否真的陳述了確實曾說過的話與曾發生的事件,只是歷史的機遇;在任何情況下,所謂「原本」的事件只會牽涉到少數人,或頂多一個局部團體的成員。更重要的是軼事經由什麼過程而被創作、流傳、編輯與修訂,因而傳遍禪宗修行人與支持者全體,直到此軼事成為具可塑性的傳說傳統的一部分;在整個中國文化中,人們是透過此傳統而認識禪宗袓師。這是馬克瑞的禪宗研究第一定律:「它不是事實,因此更加重要!」
第四、根據有關空性6的說理,在此傳承體系中沒有任何事物是真正被傳下來的,發生在每位大師與他的繼承者之間的,只是對繼承者達到完全開悟的印可。這當然是禪宗本身的教理使然,但我們應該了解,傳承圖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各祖師的名字,而是他們之間的空間,亦即他們之間相連的線條。換句話說,被呈現出來的不僅是一連串的人物,還有每位人物和他的前一位與後一位人物之間的應對(encounter)。正如禪宗典籍常強調:沒有一個「事物」──像開悟、佛心或任何東西──真正可由一位袓師傳給另一位袓師。因為倘若有像這樣的實體,則會違反一項佛教的基本教義:此教義即否定世界上的事物與眾生具有不變的、實體的、個別的性
頁287
質。就人而言,此教義稱為「無我」(anaatman);就種種不同的存在要素而言,包括人在內,則稱為「空」('suunyataa)。這不只是哲學上的考慮,而且更是具有深刻的系譜作用的有關存在的態度:焦點不是什麼被傳遞,而是諸佛與諸袓師彼此之間的應對關係。因此,「傳承」所涉及的不是某位大師給予下一位什麼「事物」,而是對其共有的心靈成熟的認可。這是個需要特殊舞伴的宇宙舞蹈,一種在最深的心靈層次上相遇的關係。
第五、由於每位佛陀與祖師的開悟都是徹底的,在印度的諸佛與祖師以及在中國與其相當的人物,彼此間並無宗教地位的差別。這是為什麼以這種傳承所作的說明,吸引了中古時代中國佛教徒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它們把中國本土人物的權威,提升到相同於印度的前輩們。從佛教的中國化來說,亦即佛教在中國文化的適應,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個主題實際上關係到中國宗教與一般中國研究方面許多範圍的主題。但是此刻,我要你們注意,對我而言此傳承圖最顯著的特質是:它的極簡單的連續線條的同構化(homologizing)作用。
根據從過去七佛乃至中國六位袓師的連續直線來呈現禪宗,像這樣的圖被用來簡化極為複雜的文化和宗教現象。在此傳承圖中,每當建立兩位大師之間的直線關係時,整個錯綜複雜的世界,人類關係與經驗構成的繁複宇宙,其實就被排除在考慮的範圍外。從一位宗教人物的一生中的種種關係之中僅選擇一種,是否有可能概括他的特質?即使是對中國禪宗大師的匆匆一瞥也能看出扭曲的程度;在資料充足的情形下,我們有時可看見由不同的老師和事件所促成的多種開悟經驗,但是在傳承圖裡這些都被簡化成單一線條的傳承。使用傳承圖來呈現禪宗傳統──傳承圖的使用與此傳統本身是一樣悠久,因為透過傳承圖的解釋,此傳統才得以存在──是一種爭領導權的表達策略,故意地擴展某一種視察世界的方式而排除其他一切觀點。(在這篇介紹性的演講中的下一項,我將簡要地討論各種的支派與劃分,見本文頁289之後。)
第六、在我以前的著作中我已提示:「系譜模式」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禪宗透過它的「從釋迦牟尼佛乃至菩提達磨以降」的傳承過程,作歷史上的自我認識;同樣重要的是它解釋了禪宗修行的方式。這就是說,相對於基本印度的觀念,將禪修視為個人的、瑜伽的努力,以自我淨化並漸進至成佛,禪宗的系譜模式則暗示最重要的心靈培育在於師徒之間的應對(encounter)。禪宗的初學者仍花長時間在禪堂中──即使典籍往往並不費心去肯定這個事實,我們也可以確定──但是禪宗的說理和文獻的焦點,是在每位大師與他的弟子之間、或每位將成為大師的人與他的不同老師之間的對話與交談。因此不只禪宗對自身宗教史的自我認識在本質上是系譜性的,禪宗的修行本身也是如此。雖然下面的一些語詞稍後必須在這些演講中小心解釋,但是我說禪宗在本質上是系譜性的,我的意思是:它來自以系譜方式理解的應對經驗,此經驗是
頁288
關係性的(relational,依據人與人間的相互作用而非僅基於個人努力)、世代性的(generational,因為它是根據親子或師徒的世代關係而組織起來的)以及重複的(reiterative,亦即讓以後的老師和弟子在生活中得以倣效與重複)。無論中國禪宗與較早類型的印度佛教禪修之間的比較或關係如何,這箇特質群在其他類型的佛教修行中是見不到的。7
然而,依最基本的說法,我們必須認識到禪宗傳承圖的同構化作用呈現出對主題的嚴重扭曲。這是馬克瑞的禪宗研究第二定律:「每一個有關傳承的主張如果重要性越多,則其問題性也就越大。」這是指,每當我們讀到某大師與某大師在傳承上彼此聯繫,這樣的敘述大概不是真的,而且它不真實的程度正與這個人物的在宗教上所佔的特殊身分直接相關。如果很少東西是建立在這種聯繫上,則有關傳承的主張較可能是正確的。而當作出某種關於傳承的主張時,幾乎總是由名單上最後一位人物(或甚至他的弟子)所受到的獲利最大。而如果他的宗教身分必須依據傳承來解釋、他的歷史地位仰賴於繼承特定前輩們所累積的號召力(charisma),則似乎總已發生了對事實某種程度的扭曲。我用「事實」一詞應該要提醒你第一定律,它在此處仍是有關連的:傳承圖對真實的扭曲代表著某種的神話創作,而不「真實」本身幾乎無可避免地更加重要!
第七、前面我提到「每位大師與他的(男性)繼承者」,這個指稱特定性別的措詞非常適合此處。禪宗傳統是極為以男性為主的,英文「patriarchal」(指禪宗代表性人物或男性中心的思想體系)一詞的模棱兩可全適合此處了。Nancy Jay曾分析過系譜系統如何有助於合理化「把女人排除在權力與生產力的環節之外」。8在後面一系列的演講中,我們會思考在中國佛教僧團(寺廟制度)的建立過程中,禪宗以什麼樣的態度展現了統合的權力。作為男性中心的思想體系,禪宗當然還有更廣泛的有關性別的問題;直率地說,禪宗是在中國社會中壓制女人
頁289
的武器嗎?我們無法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或進一步提出真正的答案,但是這個主題一旦出現,我們當然不應迴避。儘管如此,這個認識就不同的或更廣的意義而言,是有幫助的。對於前述問題下列幾種變形,我們可以處理得更好:禪是壓制一般中國宗教修行人或其中的不同團體的武器嗎?這當然是令人震驚的問題,但對我而言,知識賴以被建構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傳承的方式──似乎既容許又同時壓制不同種類的觀點。我絕非對禪宗傳統、或對一般領域的佛教禪修與心靈培育有任何偏見,但是思考禪宗在中國佛教的支配地位如何削弱其他不同的觀點,似乎是我們知識分子的責任中一個明顯的部分。
在此處,讀者可能驚訝於我們從一個簡單的圖可以導出這麼多的推論,但是我向你們保證,作為學者與老師,作為專業的喉舌──或許可以這樣自稱──我可以循此脈絡繼續發揮更多!然而,我不打算這麼做,我在後面才會對禪宗的傳承圖和禪宗傳統的系譜性格作其他評論,現在來看我以這個討論作開始的原因。
二、避免「念珠」式的謬見
我在開頭說過,對傳承圖所作的評論主要是一種預防藥,預防我想避免的一類解釋。簡言之,我的意思是:每當有人以和傳承模式一致的方式來描述禪宗時,他在冒著僅僅複述或複製整個系統的風險。他並非進行原創性的分析研究,他可能只是在複製一個繼承來的符號系統,他可能只是對此系譜模式作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更動。在此情形下對圈內人/圈外人的不同做個明確的區別是有用的:那些被在禪宗的知識結構內運作的修行人視為理所當然與自然的,以及為了成為袓師傳承中的一員所必須的東西,對於置身禪宗領域外(即使只是短暫的)的觀察者與分析者來說,都變成智性上的病症。從禪宗修行立場來看可能是絕對必須的,若換從智性分析的立場來看,卻是對領導霸權被動的屈從,是缺乏自省的智性上病症的感染。
那麼,我們現在不該做什麼?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如何認清我們是在什麼時候落入錯誤的模式,或有這樣的危險?
從這個觀點來看,問題相當簡單:每當我們根據大師代代相傳的直線繼承關係來對禪宗作出解釋的時候,我們是在冒著犯下我所說「念珠」式謬見的險。這是歷史著作中「偉人」謬見的變形,在這種謬見中人們把過去史實的繁雜細節以少數英雄人物(男性)的銳意努力來解釋(特定性別的用詞再次被合理化)。9就禪宗研究來看,這個傾向可見於許多著作如何使用敦煌寫本來補充對禪宗的認識而非徹底改變對禪宗的認識。敦煌寫本發現於本世紀初,然後散布到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它包含了禪宗文獻在第八到第十世紀間的橫斷面,剛好在宋代編輯上的齊一化(homogenization)發生以前。敦煌寫本的使用,讓學者們得以採用敦煌寫本未發現前不可能有的方法,來探索早期的中國禪宗,而且敦煌寫本的分析,在整個二十世紀引起學者的關注。(不
頁290
只在禪宗方法,還有其他領域的佛教和道教研究,以及其他領域的史學和社會學的分析)。然而依我看,來自敦煌寫本的證據大都只被用來在原有的傳統圖像上加繪一些更美的特點,只是在前述的系譜模式上加添知識上引人矚目的細節。於是學術界的努力,集中在使用敦煌寫本、並結合其他證據來為菩提達磨、慧能和其他個別的人物描繪出更鮮明的肖像,而沒有在實質上改變用以呈現這些人物的架構,當然也沒有在一開始便試圖找出導致他被納入系譜模式的文化與宗教動力。當然有例外──柳田聖山和Bernard Faure是最值得注意的──但他們是相當罕見的。我並非建議我們絕不能把傳承的描述納入我們在禪宗方面的著作中,絕非如此!只是我們這樣做時,應該知道利用它的理由,而且覺察到相關的風險。討論禪宗而不去用與傳承相關的觀念,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相信,禪宗在其最深層面是一套具有系譜性質的現象,因此前面所說的「不可能」是嚴格字面意義上的「不可能」──而且如果依靠證據向前推進時,我們可以經由不斷地轉換焦點和觀點而獲得最多的好處。犯下念珠式謬見是固定保持單一的姿勢而不自覺,我們不應僅僅改換成另一個停滯的姿勢,而應設法從數個角度去觀照主題,以不同面向的解釋能力來面對它。
三、一個權宜的設計:禪宗的各階段
在東亞佛教中,以下列三種類型來討論是很平常的,此即凡愚眾生的錯誤見解、覺悟的諸佛所體解的絕對真理,以及後者為教化前者所用的權宜解釋。在這篇導論的其餘部分我計畫要做的是屬於第三類,亦即對中國禪宗發展的權宜解釋,它將有助於我們進行討論。(很抱歉,我僭越地佔了「覺悟的」地位。當然我佔此位是有限制的,是相對的!)我提出下面的看法並非只作為上述傳承圖之外的唯一選擇,而是幾個選擇之一。它可望成為有用的權宜方便,就像佛陀用來引導他的聽眾更深入了解善巧方便。
在頁296有個簡單的圖表以相當不同於前述傳承圖的方式來描述禪宗。正如我用此圖表的目的與禪宗傳統使用傳承圖的目的是不同的,此圖表的格式和內容也與傳承圖的不同。
在傳承圖列出了個別人物的名字,然而我的圖表中卻列出禪宗發展中被給予了名稱的各個階段或趨勢。這些名稱並不是所有其它關於禪宗的著作都普遍接受的。它們之間的界線也具有爭議性。我不想隱瞞這些不確定的情形,而對你們宣稱這些術語和時期劃分在我的演講中被拿來使用是完全沒問題的;相反地,我要人們注意在此處被如此特別而明確地命名的各階段之間的界線所存在的模糊性。透過思考這些任意定出的事物其邊緣兩側之間的區別,我們將可見到其效用。
雖然各個被命名的階段有列出某一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各階段並非是指涉特定
頁290
的個人本身,而是指涉透過種種資料而得知的宗教活動的風格或整體結構。用以描述各階段特徵的主要模式之一,當然是舉出一系列的大師,亦即在傳統的傳承體系中所謂的袓師,他們的功能是作為具有特定宗教身分的代表性人物。這些人(男人,偶爾女人)擔任了開悟行為的典範,他們的故事一再被敘述以便依照某種格式(pattern),來塑造那個世代的弟子們的行為。(即使襌宗所包含的開悟的自發性中,超越了格式化的行為,但這種捨棄格式的本身也必須被放入格式,以便在真正有天賦的修行人能模仿或甚至解構(deconstruct)、重組(re-figure)以前,讓它能被理解並拿來當作模型)。有關這些代表性人物的資料,以及教義解釋與其他種類的資料,是同時以口傳及書寫的典籍來流傳。因此禪宗的各階段可以從多個面向來描述:可作模範的代表人物、他們活動的地域和時間、以及敘述他們的活動與表達他們的教法的典籍等等。在每個階段的摘要中會簡短地提供這類資料。因此,傳承圖與本圖表的基本差別是:傳承圖傾向於把所有人物同構化,這些人物被描寫成在單一教團(confraternity)中同等開悟的諸典型──依據一種富有意義卻一元化的宗教模式來促成/限制對他們的了解。然而本圖表是沿著時間編年的軸線來尋求各階段間性質上的差別,以助於多元化的觀點和理解模式。本圖表的目的是要產生有意義的區別,而不是要肯定連續不斷的袓師權威。按照Michel Foucault的說法,這種對有意義的區別之探索,落在當代學術論述的脈絡中,或許也是為了追求權力;但是傳承圖以更露骨的方式呈現出「對正統的企求」。
在此,你可以指出傳承圖並非單一直線發展的,在某幾點它分化成雙線,乃至細分為禪宗五「家」。當我在前面已經致力於闡明傳承圖起著同構化的作用,也闡明作為其基礎的一些宗教上的假設,那麼現在我要如何解釋這些分化?
我們在後面會詳細討論這些狀況中的大部分,但基本上來說,有了這些例外,我們更能夠證明前面的觀點。正如Bernard Faure所主張的,慧能與神秀這兩位南、北宗的代表人物在傳統禪宗的意識形態(ideology)中並不是互相隔絕的兩個人,而是彼此糾結的一對。以Faure刻意使用的法文術語來說,即“duel”(“duel”同時表示二元性與競爭性)。簡言之,若不提被歸為北宗的漸悟教義,則無法解釋屬於南宗的頓悟教義。(這種頓、漸的簡化解釋未免太不足以解釋歷史上的慧能和神秀的教法,然而我恐怕這個缺陷將在中國禪宗的描述中永遠持續下去。)你將注意到這兩宗連同牛頭禪一起被納入第八世紀的「早期禪宗」階段──這是個刻意的歸類,用以指出這三個宗派的相似勝過相異,或至少它們的宗教身分是如此緊密相連以至必須一起陳述它們。沒有一位神秀的弟子被納入禪宗傳承圖中(在頁285已提到),在傳統主義的禪宗記載中,他們不被列入考慮中;此處他們饒富意味的缺席,正足以凸顯可上溯到傳說中的(亦即非真實的,但也因此而更重要)慧能的「正統」世系單線發展。雖然
頁292
我暫且不論證以下這一點,但是臨濟與曹洞的區別意味著同樣的「duel」關係,也就是說,配合在一起成為既相對比又相競爭的二元關係。但是我必須更加上一層複雜性,這個圖可能很容易被忽略的一項特別的細節:它試圖表達不同階段在時間上所具有的回顧性的(retrospective)特質。請注意在每個階段的名稱下實際上有兩個年代項目,第一是界定大約的起訖點的一組年代,第二是一個特別的「指標年代」(target date)。後者是我的嘗試,以指出特定階段的名聲在禪宗的整體記憶中固定下來的時刻。在方法上,無疑地我應受責備,因為我用整體記憶的措詞來討論,並有把禪宗實體化而當作活的有機體──在Fischer的《歷史學家的謬見》一書以及更晚的理論方面的文獻中,這兩種錯誤都被上了枷鎖。不過無所謂!我相信這是給本圖表的一件有用的附加物。
若沒有這些指標年代,讀者可能會以為本圖表在描繪一連串的歷史因果關係,但是它其實是在描述禪宗的不同階段的追溯的特性。我們應該從一開始就認識到任一組過去事件的時期劃分,代表了一種重建的行動,不僅是資料的重新組織與整理,更是把過去事物,整個重建為我們想像力所造的意像。創造過去事物的意像並沒有錯──我的確相信這是作為歷史學者的任務,無論是專業或業餘的歷史學者,以我們知道最佳方式去想像過去。但是我們應該保持對下列事實的認識:整理從第五到第十三世紀的發展情形,難免涉及這種重新創作;天真地相信我們只是在整理資料以求便利,而在此過程中並沒有作實際更動,這種信念無法使我們脫離重新創作的困難。
其實,這種追溯的特性到處充斥在禪宗的傳統中。我們一再發現我們所處理的,不是在特定時間所發生的事,而是被人們認為是已經發生了的事。我們處理的不是事實和事件,而是傳說與重建,不是成就和貢獻,而是歸屬(attributions)與遺產(legacies)。決定日後的宗教的與社會的實踐的是傳說與重建,而不是想像中的真實事件。不是真的,所以更加重要。
因此,各階段的指標年代不是用來代表它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或由知名或不知名的歷史人物的關鍵性行動所成就的轉捩點。這些指標年代所表示的是,我要嘗試去說明,對於當時的參與者,尤其是對後來的追隨者來說,從什麼時候起,那個時代中開始出現某些比較明確的情節與主題。因此這些指標年代是我自己推論的產物,是甚可爭議的,而且必然是其他許多學者不能接受的;這是我倚仗自己的想像力敢去的最遠的地方,並非每個人都願意跟我到這麼遠。不過,我不會在此久留──只久到足以建立以下的論點。
這個論點是,正如我對中國禪宗從菩提達磨到宋代的各個假設性的(supposed)階段給予種種的名稱是屬於後來的解釋;同樣地,在豐富而多面的傳統中,中國的參與者必然也對他們所繼承與經歷的事物給予他們自己的解釋。「指標年代」只是我嘗
頁293
試要用來說明在這個過程裡的某些關鍵時刻,亦即大家普遍熟知的並影響後世的關鍵時刻。因此,645年是當菩提達磨的事蹟與那部被認為是他所作的典籍首次被一部極重要的中國僧眾的傳記《續高僧傳》所提及的時刻;780年標誌劃時代的《六袓壇經》及它對早期禪宗史深具影響力的改造出現的時刻;952年代表了《祖堂集》中禪宗的「機緣問答」爆發性的出現;1134年指出大慧宗杲(1089∼1163)使用「看話」(大約相當於英文資料中所認識的「公案禪」)的禪修方式初次經歷成功的年代。10各個指標年代只是對中國禪宗傳統的整體認識中的各主要轉變作方便的標示。在心中有了這些考慮,並且為了對其餘的演講所涵蓋的主題能有較好的觀察角度,讓我們更詳細地觀察圖表中所列的階段。
「原形禪宗」是指圍繞著菩提達磨和慧可的、詳細情況不明的修行團體。這個團體似乎在許多不同的地方活動,而相關的人們自認為參與這個單一「團體」到什麼程度也不明確。由於他們無從得知他們的活動會延續成後來的「禪宗」,即使「原形禪宗」這一方便的術語也經不起檢視(只有對知道後來發展的人來說,他們的活動才是「原形的」。)我們只知道少數幾人從學於菩提達磨,大概在這位大師死後,有更多一點的人主要與慧可相聯繫。對於我們當中喜歡猜謎的人來說,菩提達磨究竟是誰
──還有他在何年代,根據誰的敘述──是困難但有趣的問題。雖然年代與情況很模糊,我們還知道在菩提達磨名下流傳的一部典籍《二入四行論》提供了禪宗修行思想體系中的核心教義。
「早期禪宗」代表了這個學派或最後將成為學派的東西,首次明確而周詳地陳述以傳承為基礎的意識形態的時期。然而事實上,敦煌寫本與傳統禪宗的記載,也包含了相異於這個時期、種類多得驚人的公式化表達(formulations);而且隨著禪宗運動的成熟與結晶,顯然大量的實驗,亦即對一般接受的主旋律所作的變奏曲,正在進行。與後期禪宗典籍相比,這些公式化表達可能是古怪的,但並非特別神秘難懂;這個時期的著重點在能夠明白地表達這個新形式的佛教教法,而不是在創造完全不同類型的表達方式。與原始禪宗相比,早期禪宗的階段有很穩定的活動區域:道信與弘忍在黃梅的幾乎同一地點待了剛好半世紀,也許還可以再加上神秀在不太遠的玉泉寺待了四分之一世紀。當然,隨著禪宗在長安與洛陽這兩個帝都的擴展,事情變得更複雜。
頁284
我將在第二次演講中,對東山法門連同著菩提達磨與原始禪宗一起討論,在更後一次的演講我將把南、北宗與牛頭宗放在一起。把最後三者放在一起是很恰當的,這是因為它們彼此間對話,而且它們在歷史身分上被假定的差別,絕不像禪宗傳說要我們相信的差別那樣明顯。把東山法門劃分出來成為完全個別的階段是十分恰當的,但是我希望,在此加上這些說明──並以不同的方式組織圖表與演講──足以顯示相關界線的權宜性質。
在「中期禪宗」的階段發生了一個重要的事件:「機緣問答」(encounter dialogue)出現了,亦即禪師們被描述為以個人獨特的方式與弟子們對話。11這是禪宗似乎真正成為禪宗的時候,它與這些著名人物相關,如馬祖與石頭、百丈與懷海、臨濟與曹山與洞山,人們不斷複述這些故事以作為看似矛盾實為開悟的行為的典範。此時宗教實踐的重心由個人在禪堂的努力穩固地轉移到令人費解的發問型態,力求避免一切表層意識的、邏輯的格式。自發性是其法則,反因襲的行為是其規範。或者,它看起來是如此──因為在此我們必須考慮的,不只是機緣問答作為宗教活動主要模式的重大意義,還要考慮一個困難的問題:即這種自發的相互作用在什麼時候真正地被實踐。我們會發現禪宗傳統中最有名的幾個故事。被假定發生的時間,與它們首次以書寫的形式出現的時間有相當大的差距。而且,我們得考慮這些故事作為口傳與書寫的文獻所具的效力。
過去我與其他作者曾把中期階段稱作禪宗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或「古典時期」(classical period),而且我仍然在某些場合使用後者。不過,我這樣做只限於下列情況:我所指的並非真正發生在第八到第十世紀的某些活動與事件,而是這些活動與事件被回顧後的再創作,它是宋代禪宗信徒心中想像出來的唐代傳奇人物的身分。只有馬祖和其他唐代人物的時代過去後,當他們的身分被重新塑造以符合宋代禪宗的需要時,他們才代表典範時代。我的一些同事──主要是Robert Buswell與Griffith Foulk──曾這樣寫道:宋代禪宗應被視為真正的「古典」時代,就此時期禪宗的整體活動與一般地位來說,他們當然是對的。
宋代禪宗代表了中國禪宗的「顛峰典範」(climax paradigm),此時這個傳統擬定了它的最終形態的基本輪廓。以前的作者傾向於忽視這個時期,部分是由於想要探
頁285
索更「有創造力」的唐代大師們。宋代於是被貶抑為中國佛教衰落以及僵化為制度上的形式主義的開始。但由於宋代宗教大概已成為研究現代以前中國宗教的主要焦點,這種態度正在改變。也由於認識到曾經傳遍東亞乃至如今已遍及世界的基本禪宗型態是在宋代發展成的,我們對宋代禪宗的印象也已改變。這點可見於大慧宗杲的一生與教法,他是中國禪宗史上「看話」或公案禪的最偉大提倡者。我們也將審視曹洞傳承中所倡導的沈思內省,我們要小心不接受臨濟把這種修行貶低為僅僅是「默照」。最後,我們將發現臨濟和曹洞的方法呈現出一個“duel”,與第八世紀頓、漸之爭的“duel”極相似,也與歸為菩提達磨所作論著中的「二入」觀念互相共鳴。但是這超過了我們現在的進度……讓我們回到菩提達磨本人的傳奇記載,先來看看禪宗是怎麼發展的。
頁297
| 附錄:中國禪宗各階段簡化圖表 | |
| 原形禪宗: | 菩提達摩(大約卒於530年) |
| 大約500∼600年 | 慧可(大約485-555或574年以後) |
| 指標年代:645年 | 《二入四行論》 |
| 摘要: 華北許多地點;基於佛性的修行;未知有傳承理論。透過傳統典籍與敦煌文獻而被認識。 | |
| 早期禪宗: | 弘忍(601∼74),神秀(606?∼706) |
| 大約600∼900年 | 慧能(638∼713),神會(684∼758) |
| 指標年代:780 | 北宗、南宗、牛頭宗 |
| 《六祖壇經》 | |
| 摘要: 幾個定義寬鬆的派別/團體,對於「觀心/看心(contemplation of the mind)」有不同的方法;與原始禪宗的關係並不清楚;傳承理論出現於早期;於早期禪宗的末期成為起統一作用的意識形態;透過敦煌文獻與傳統資料而被認識。 | |
| 中期禪宗: | 馬祖(709∼88),石頭(710∼90) |
| 大約750∼1000年 | 臨濟(卒於867),曹山,洞山 |
| 洪州宗與湖北宗,五家的前身 | |
| 指標年代:952年 | 《祖堂集》 |
| 摘要:「機緣問答」出現,成為修行和說法的主要方式,以口語形式記錄下來並暗示著系譜模式的宗教修習;不存在於敦煌文獻,但可透過宋代典藉而得知,在宋代被理想化成為黃金時代。 | |
| 宋代禪宗: | 大慧(1089∼1163),宏智(1091∼1157) |
| 大約950∼1300年 | 五家,臨濟與曹洞宗 |
| 指標年代:1134年 | 《碧巖錄》 |
| 摘要:禪宗興盛的極點,在僧團建立的過程中,作為首要之經營上的意識形態;在高度儀式化的宋代環境中銘刻著以開悟的自發性行事的唐代大師們的意像;片段的機緣問答被收集,編輯以作為開悟活動的先例,並用來當作禪修探究的主題。 |
Looking at Lineage: A Different Way fo Prisenting Chan Buddhism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Indiana
McRae, John.R.
Summary
The goal of this essay is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how we should look at Chan Buddhism. I argue that there should be a multiplicity of perspectives and a certain fluidity of analytical typologies in doing so, and that we should consciously work to escape the structural limitations imposed upon us by traditionalistic approaches and by the subject matter itself. By traditionalistic approaches I mean those implied by Chan lineage diagrams, which have a semiotic impact as a medium of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irst, the Chan lineage scheme is a combined product of Indian and Chinese culture. This observation undercuts the chauvinistic and essentially meaningless assertions that Chan is the "most Chinese" of all the Chinese Buddhist schools. Second, there are distinct polemical implications in the definition of Chan as a "separate transmission outside the scriptures," as fundamentally more authentic than all other Buddhist schools. Third, what counts in the Chan transmission scheme are not the "facts" of what happened in the lives of Sakyamuni, Bodhidharma, Huineng, and others, but rather how these figures were perceived in terms of Chan mythology. What is of the greatest consequence here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at mythology was generated and circulated, edited and improved, and thus transmitted throughout an entire population of Chan practitioners and devotees. Fourth, based on the rhetoric of sunyata, or emptiness, there is nothing that is actually transmitted in this transmission scheme. What occurs between each teacher and his successor is merely an approval or authorization of the successor's attainment of complete enlightenment. Fifth,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of each Buddha and Patriarch is complet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of religious status between the Indian Buddhas and Patriarchs and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This is very important in terms of the signification of Buddhism, in that it allowed Chinese Buddhists to venerate and emulate culturally Chinese role models. Sixth, the "genealogical model" is important for its impact on how Chan spiritual practice itself is carried out. That is, the Chan genealogical model implie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takes place in the encounter between each teacher and his student. Seventh, the gender-restricted terminology of "each teacher and his successor" is very much appropriate, since the Chan tradition is overwhelmingly male-dominated. Although I do not have space to consider these subjects in this paper, we should be sensitive to ways in which the lineage format both allowed and suppressed different types of perspectives, and how Chan school's dominance in Chinese Buddhism may have mitigated against alternative viewpoints.
The result of these deliberations are distilled in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 any time we pretend to explain Chan in terms of lineal successions from one great master to another, we run the risk of committing what I call the "string of pearls" fallacy, in which the evolution of Chan Buddhism is described in terms of a sequence of individual masters like pearls on a string. This is to misrepresent historical and religious reality, which are both far more complex and interesting than this simplistic model would imply.
Key words: 1. lineage 2. school 3. genealogical 4. encounter dialogue 5. patriarchal
1 我要向聖嚴法師、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李志夫教授、陳秀蘭祕書以及研究所全體工作人員表達我的深切謝意,感謝他們在我目前在臺灣做研究期間給我友善的幫助。這篇論文是準備用來以演講的方式發表於該研究所,以及6月19∼21日在西班牙瓦倫西亞,由日本曹洞禪宗贊助的研習會。我希望將一系列六篇論文出版成書,這是其中的第一篇。我也要感謝關則富把這篇論文譯為中文。
2我指宗派時用“school”一詞是因為它意思含糊。很重要記得中國佛教宗派幾乎沒有制度組織上的要素。因此我嚴格避免用“sect”或甚至“denomination”的字眼。
3讀者可參閱柳田聖山著《初期禪宗史書ソ研究》(京都:法藏館,1967年),pp. 265∼80.
4見Robert Sharf, “The Zen of Japanese Nationalism” in Donald S. Lopez, Jr., ed., 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107∼60.
5 Gregory Schopen指出孝敬的表現並不都意味著當地固有的影響;見他的 “Filial Piety and the Monk in the Practice of Indian Buddhism: A Question of ‘Sinicization’ Viewed from the Other Side,” T’oung Pao 70(1984): 110∼26.
6 這是大乘佛教的一個基本觀念丕,它會一再出現;一個很好的概述見乎Paul Williams, Mahaayaa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89)。至於對中國禪宗細節的敘述,則可見Heinrich Dumoulin, S. J., Zen Buddhism: A History, 2 vol., trans. by James W. Heisig and Paul Knitter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8∼89),特別是1994年第一卷的修訂本,包括它的新加的附錄。
7見McRae, “Encounter dialog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iritual path in Chinese Ch’an,” in Robert E. Buswell, Jr., and Robert M. Gimello, eds., Paths to Liberation: The Marga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n Buddhist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pp. 339∼69.
8 見Jay, Nancy B., Throughout Your Generations Forever: Sacrifice, Religion, and Pat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我要感謝Andrew Junker,他目前是印第安納大學宗教研究生,他介紹Jay的著作給我。
9見David Hackett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0).
10 很重要地,這是妙道比丘尼在大慧指導下開悟的年代。關於這個重要的事例,見Miriam Levering,“Miao-tao and her Teacher Ta-hui,”即將出版。就女人在禪佛教中的廣泛論題,見Levering’s“Stories of Enlightened Women in Ch’an and the Chinese Buddhist Female Bodhisattva / Goddess Tradition,”in Karen L. King, ed., Women and Goddess Traditions in Antiquity and Today, Studies in Antiquity and Christianit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7), pp. 137∼76.
11“Encounter dialogue”是我在下書的翻譯中首先使用的字:“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corded Sayings’ Texts of the Chinese Ch’an School,”tr. from Yanagida Seizan,“Zenshu goroku no keisei”(禪宗語錄ソ形成),Lewis Lancaster and Whalen Lai, eds., Early Ch’an in China and Tibet, Berkeley Buddhist Studies, no. 5 (Berkeley, CA: Lancaster-Miller Press, 1983), pp. 185∼205.“Encounter dialogue”是日語術辭kien mondo「機緣問答」的翻譯,但是相應的漢語很少見於禪宗書籍,請了解是個現代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