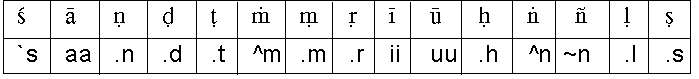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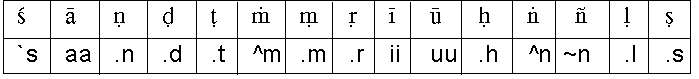
頁74
前言
在梁《高僧傳》中,作者慧皎原本要分該傳為八科,後來卻發現「經導二技」,在化俗上有其價值性,才增加為十科,如其所云:「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卻尋經導二技,雖於道為末,而悟俗可崇」。換言之,這「經師」與「唱導」二技,很可能在當時是非常盛行,因此他才會讚嘆此二科有化導眾生的作用,又稱此二科為「技」,很明顯的表示它們是「技術」或「技藝」,也許被認為是度眾的方便技巧;然而於修持法門的排行榜上,慧皎則認為是「於道為末」的敬陪末座了。但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有待商榷,因為在該傳中的「誦經」、「經師」、「唱導」三科有交集之處,事實上也很難明確的劃分界線。若勉強的區分大致可歸類:「誦經」篇是僧人以誦持某特定的經典為個人的修行依據,有時會有感應,並隨緣的度眾; 然「經師」則是「轉讀」、「諷詠」經典,並配合音聲梵唄之技藝;「唱導」即是宣唱法理於齋會中以化導眾生。 事實上套用現代語言,後兩者都是以「音聲佛事」為業 -- 以誦經、禮懺、宣導度化眾生,然而「誦經」篇中的僧人大都以「誦」或「諷詠」經典為個人修持的依據,似乎不是以誦經為業。 但詳讀「誦經」與「經師」二篇之後,筆者發現這兩篇有多處雷同之處,也難怪在《續高僧傳》中,道宣把「誦經」改為「讀誦」,而「經師」與「唱導」合併於「雜科聲德篇」了。[1] 然本文僅探討初期中國佛教中的「音聲佛事」對當今佛教中「禮懺佛事」的影響,故以梁《高僧傳》中相關的三科為討論的中心,以下將這三科一一介紹。
註1:T.50/2060, PP.685,700.
頁75
一、誦經科
該篇中收集了正傳 21 人,旁出附見者 11 人。 [2]該篇中記載的僧人大都是苦行、誦經、禮懺、習禪而感得鳥獸集其左右、或老虎蹲其前、異人獻寶、甚而菩薩現前。他們所誦之經典有:正法華經、古維摩經、十地、思益、大涅槃、金光明、首楞嚴、大品、進而金剛般若經等。[3] 正傳 21 人中就有 16 人誦持《法華經》,可見《法華經》是六朝時代僧侶的寶典。其次是誦持《古維摩經》的有 7 名,也有以法華、維摩二經為主要修持經典,以其餘經典為修持依據者其數尚少,以下略舉數例以解之。
釋普明 (晉代約 371-455) 以「禮懺為業」,誦「法華維摩二經」,每誦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唱樂,又善神咒所救皆愈」。[4] 普明所誦持的法華經應是鳩摩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406 A.D.譯),因為羅什譯本的第二十八品是 <普賢菩薩勸發品>,相似於竺法護譯的《正法華經》(286 A.D.譯) 的二十六品 <樂普賢>。該<勸發品>品提及:
「是人若行若立讀誦此經 ...若思惟此經...我復乘白象王現其人前..」。[5]
很奇怪的,在竺法護譯的<樂普賢>品中卻無「乘象立其前」之說,而是:
「一心勤修正法華經,書持經卷常當思惟一切不忘....臨壽終時面見`千佛'...不墮惡道」。[6]
此差異很有可能是他們所持的原文本就有不同了。另外,由竺法護的該譯文中得知「千佛」的觀念早在西元三世紀已存在中國佛教中了。又傳文中明言「勸發品」,很明顯的普明所誦持的《法華經》即是羅什的譯本了。 再者,「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唱(倡)樂」一事,也在該經中發現相似之事。羅什譯的《維摩詰所說經》(406 譯) 中亦提及:
註2:T.50/2059,在慧皎自製的目錄中在「僧覆之下有附見慧琳」見P.421c,但於僧覆的傳文中卻無有慧琳的敘述,見P.407c,故筆者將慧琳刪除,只列11人。
註3:大品經是《大品般若經》的簡稱,見《法寶總目錄》No.1, P.208c.
註4:T.50/2059, P407b.
註5:T.9/262, P.61ab.
註6:T.9/263, P.133bc
頁76
「持世白佛言...我昔住於靜室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絃歌來詣我所。」[7]
支謙譯的《維摩詰經》(223-253 年間譯) 也有相似的譯文。 [8]這兩則感應之事,無異在表達虔誠禮誦不僅感得天人、菩薩讚嘆,而且也是入道法門之一,又普明善於神通咒術以救世濟人,因此不難揣測他是個有道的高僧吧。
另一則傳文也與普賢有關,應該也是誦持法華經之故吧。 釋道冏 (約卒於 宋 443)「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進修禪業...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 倏忽不見」。 [9]道冏一向主修法華,又念觀音[聖號],並數度舉行「普賢齋」,可見他也是個普賢菩薩的感應者了。
中國「齋會」的流行可能始於西晉,因為西晉時竺法護所譯的齋經被記載於《出三藏記集》(445-518年 又稱僧祐錄):
「菩薩齋法(經) 一卷,舊錄云菩薩齋經,或云賢首菩薩齋經,右 64部 凡116 卷今闕,竺法護譯」。[10]
賢首與普賢都是華嚴經中的大菩薩,有賢首菩薩的齋經,應該也會有其它菩薩的齋法才對。 於《彥悰錄》(602年)竟然也發現一些有關齋法的「闕本」(舊錄有目而無經本) 記錄:
「佛悔過經一卷 晉世竺法護譯、菩薩悔過法一卷 晉世竺法護譯,菩薩齋法一卷 (一名持齋,一名法齋) ..... 菩薩受齋經一卷、菩薩受齋法一卷、六齋八戒經」。[11]
可見在晉朝這些齋法與悔過法可能流通過,而隋代的《彥悰錄》中這些有目無本的經都是由「舊錄」抄襲下來的,因此不難推斷齋會、懺法可能始於晉代之前,而盛行於南北朝,才會在梁《高僧傳》中出現不少不同名稱的齋會,例如:禪齋、聖僧齋、苦行齋、捨身齋、普賢齋、七日齋、觀世
註7:T.14/475, P.543a.
註8:T.14-474, P524b.
註9:T.50/2059, P.407a.
註10:T.55/2145, P.9b
註11:T.55/2147, PP.175a,177ab
頁77
音齋、金光明齋、盂蘭盆齋、三千僧齋會、無遮大會等,可見「齋會」在第五、六世紀時是非常盛行的法會。
漢譯的「齋」字相似於梵文的 Uuposatha (Upo`sadha, Upavasatha),譯為「布薩、齋戒、靜齋」等意。[12] Upo`sadha 有「purity (清淨), confession of one's sins (發露懺悔自己的罪)」之意,並引申為三意:淨化身、口、意三業,過午不食與不食非時之食,和法會中的齋食。 [13]又 Upo`sadha 有 confess (自白、懺悔) 之意。[14] 可見「齋」在印度佛教的傳統中是淨化身心與發露懺悔之意。 又由上述的經錄與梁僧傳中得知,六朝時代的齋會大都與懺悔分不開,例如【釋玄高】傳記載:「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15] 顯然中國早期的佛教,在飯食的齋會中是有懺悔三業的儀式,與印度佛教的傳統是相似的。然現今佛教法會中的齋食,是否有懺悔的心情,則就因人而異了。
又釋法恭 (亡於宋太(泰)始年間 465-471) 春秋八十,「誦經三十餘萬,每夜諷詠,輒有殊香異氣」。[16] 漢文「諷」即「誦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17] 「詠」則是「歌也、長言也」。[18] 顯然地,誦經即是諷誦,也就是要拉長音聲、有節拍的唱誦。 法恭誦經而感得殊香異氣,此乃表示他也應是個以誦經而入道者。
不僅齋會與懺悔有關,事實上誦經與禮懺也是息息相關的,在傳文中時常出現「禮誦」、「懺誦」之詞。 例如釋弘明 (403-486) 的實例:
「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又一小兒來聽明誦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圊中 (廁所),聞上人道業,
註12:見赤沼智善,《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京都:法藏館,1931, P.714b.
註13:Japanese-English Buddhist Dictionary, Daito Shuppansha, 1965, P.246.
註14: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II: Dictionar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5, P.147b.
註15:T.50/2059, P.397b.
註16:T.50/2059, P407c.
註17:見《中文大辭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3,普及版,No.8,.1078c. 「倍文」即是「背誦書文」,「倍」通「背」,見上列辭典,No.1, P.1049b.
註18:同上辭典,No.8, P.927a.
頁78
故來聽誦經...」[19]
另道嵩 (宋) 也是「懺誦無輟」,僧侯 (396-484) 則是「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又「誦法華維摩金光明」。而慧彌 (440-518) 也是「曉夜習定,常誦波(=般)若,六時禮懺」。[20] 此中的「上人」「禮千佛」、「懺誦」都是當今中國佛教界普遍使用的語詞與儀式。
在上面釋弘明的例子中受報的沙彌現身來聽誦經,且稱弘明為「上人」,此乃表示該僧的道行德業,足以感動幽冥界的眾生。「上人」原是中國儒家傳統上對「優異人」之稱呼,<新書脩政語>云:「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21] 該語詞也出現在佛教的經典中,例如鳩摩羅什譯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403-404譯) 提及:「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亦隨喜,所以者何,上人應更求上法」,[22] 可見般若經中指的上人是「發菩提心者」。 又佛教辭典《釋氏要覽》(北宋 1019 道誠撰) 也解釋:「上人,古師云,內有智德,外有盛行」,[23] 此似乎有「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涵意。 該語詞原來已在羅什的譯本中出現,難怪慧皎 (497-554) 的僧傳中也有「上人」之詞,可見「上人」的用法始於儒家,進而被使用於六朝時代的佛教界。 然該語詞也在目前佛教界中時有所聞,徒眾們稱呼自己敬愛的師長為「上人」,這原來是有其典故的,至於現代人對它的定義是否與古人相同,就不得而知了。
「禮千佛」也是現今佛教中常舉行的法會之一,尤其是在中國的農曆年間,大部份的佛教寺廟都會有「禮三千佛」或「禮萬佛」的法會,而「禮千佛」這名詞竟然也出現在梁僧傳 <誦經篇> 釋僧辯 (420-492) 的傳文中,可見它必定有其源流,如傳文:
「誦法華、金剛般若....誦法華日限一遍...禮千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24]
註19:T.50/2059, P.408a.
註20:T.50/2059, P.408bc.
註21:見《中文大辭典》,No,1, P.306b.
註22:T.8/223, P.273c.
註23:T.54/2127, P.261b.
註24:T.50/2059, P.408b.
頁79
「千佛」的名詞早就出現在西晉竺法護的譯經中 (見上注解六)。禮千佛必須依據諸佛名號經典而禮拜,因此該類經典早在西晉時代已譯出,據《僧祐錄》,竺法護曾於太始中 (265-274) 至永嘉二年 (308) 間譯《諸方佛名經》一卷與《十方佛名(經)》一卷,但已在僧佑時代就「闕」失了。[25] 又在該錄的「新撰失譯 - 雖缺譯人,悉是全典」,且「今並有其本,悉在經藏」中收集有 14 部佛名經:[26]
「有稱十方佛名得多福經一卷 (抄)、三千佛名經一卷、千佛因緣經一卷、稱揚諸佛功德經一卷 (抄三卷稱揚諸佛功德經)、過去五十三佛名(經)一卷 (初藥王藥上觀,亦出如來藏經)....賢劫千佛名經一卷......滅罪得福佛名經一卷。」[27]
上列引文中的佛名經,在僧祐時代都是流通的,只是遺失譯者罷了。但有一部與上述同名的《千佛因緣經》竟然被收集在大正藏第十四冊,No.426經,又掛名是鳩摩羅什譯的。 該經在《僧祐錄》、《法經錄》、《彥悰錄》、甚至《大唐內典錄》中均列入「失譯經目」中,[28] 直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695 明佺撰) 才歸於羅什的名下,[29] 很顯然的該部經實非羅什所譯。[30] 又收集在大正藏第十四冊中有關佛名的經典就有十多部,其中三部「失譯」--- 遺失譯者的過去、現在、未來千佛名經 (No.446,447,448經) 有可能相似於上面引文中的「三千佛名經」。
另在《僧祐錄》卷十二,序文「千佛名號序 出賢劫經 沙門竺曇無蘭抄」:
「賢劫經說,....八萬四千度無極法,當來賢劫一千如來,亦得入也。...佛為喜王說諸佛號字,號字一千數之有長。而興立發意二品重說,皆齊慧業而止,以此二品撿之。有以二字為名者,三字名者,有以他字足成音句,非其名號,亦時有字支異者,相(想)梵本一耳,將是出經人,轉其音辭令有左右也,長而有者,或當以四五六字為名號也。...余今別其可了,各為佛名,意所不了,則全舉之,又以字異者注之於下,然或能分合失所,深見達士,
註25:T.55/2145, P.9a.
註26:T.55/2145, P.21b,P.32a.
註27:T.55/2145, P.22b.
註28:T.55/2145, P.22b, T.55/2146, P.121a ,T.55/2147, P.153a ,T.55/2149, P.304a.
註29:T.55/2153, P.377a.
註30:對於羅什的譯經,筆者曾於拙著《請觀世音經譯本考》中討論過。
頁80
其有覺省,可為改定,恕余不逮。」[31]
該序文是解釋《賢劫經》中的一千佛也能入無極法,[32] 因而有卷六的「千佛名號品」,在該品中佛號都是三字為一名。[33] 但在卷七「千佛興立品」與 卷八「千佛發意品」中,對佛號的解釋,漢文字數就不定了。誠如序文中所說,有二字、乃至五、六字,其梵本都是一樣,只是譯者繁簡的解釋不同罷了。「興立品」是介紹每一佛的種性、父母、與成佛時的國土、所度眾生的人數。另「發意品」即解釋諸佛修道因緣,[34] 此應是序文中所說的「慧業」。 該序文是竺曇無蘭抄出,他於東晉 381 - 395 年間在中國譯經,[35] 又《賢劫經》之末記錄著:「竺法護於(西晉)永康元年 (300) 七月二十一日,手執口宣,時竺法友,從洛寄來,筆受者趙文龍...」。[36] 該序文自云「出賢劫經」,內文是抄的,可見原序文應附在《賢劫經》內,但現存於大正藏中的該經,卻無此序文。又竺法友是東晉時人,收到後即手抄,因此很明顯的大正藏所收的《賢劫經》是東晉時代的抄本,在當時此序文已未錄進該經中,故竺曇無蘭才會另抄出這篇序文。 此外,竺曇無蘭在東晉時抄出此序文,其動機何在? 又由其序文中的內容 - 對千佛名號字數差異的解釋,不難揣測當時 (東晉) 千佛名號的禮拜可能是盛行的,而且對千佛名字翻譯字數差異也許有所爭執,所以序文中才會說明佛名只是分別而已,不可能全舉出其意。若無流通,豈會有爭執,可見千佛的禮懺在東晉時應是流行的。
《高僧傳》中釋超辯所禮千佛的經典,有可能出自《賢劫經》,或是《僧祐錄》中所載失譯的經典之一吧,但這已無從考查,只是由《僧祐錄》所列的失譯佛名經中可反應出當時「禮千佛」的懺法可能流行一時,乃至現今已成習俗。 但是現今一般佛寺中禮三千佛所用的經本有稱《佛
註31:T.55/2145,P.82b.
註32:無極法是修行度眾的法門,見T.14/425,「二千一百諸度無極,貪婬怒癡等分四事,各二千一百,合八千四百,八千四百各別有十事,合八萬四千,以能具足度無極,便已備悉八萬四千眾要上業。」,P.12b-13a。另細節見該經PP.11b-13a。
註33:T.14/425, P.45c-50a.
註34:T.14/425, PP.55-63.
註35:見《法寶總目錄》,第一冊, P.677a.
註36:該經後記中的竺法友是東晉竺法深(286-374)的高徒,「常從深受阿毘曇,一宿便誦」,故竺法友也是東晉時代的人。見T.50/2059, P.348a. T.14/426, P.65c.
頁81
說千佛洪名寶懺》[37] 或《三劫三千佛緣經》[38], 這些經本因不同的寺廟而冠以不同的名稱,但內容都是相同的,尤其在初頁都有此 「三劫三千佛緣起,薑良耶舍譯」之言。經筆者內容的核對,發現此「緣起」即抄自大正藏中的 No.446 《過去千佛名經》中最前面的一段「三劫三千佛緣起」並附言「出觀藥王藥上經」,而此段緣起也確實抄出自薑良耶舍譯的《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39]。 不論是《洪名寶懺》或《佛緣經》都是錄自大正藏第十四冊中 No.446,447,448 的失譯過去、現在、未來千佛名經。故當今中國佛教「禮千佛」所用的經本,只是幾部失譯經的合併本罷了,又該經初頁的「緣起」也是抄自薑良耶舍譯的《觀藥王藥上經》,所以它只是一本選自不同時代、不同譯者的合併經而已。
不僅禮千佛,超辯也誦持《金剛般若經》,該經的誦持在六朝時代還似乎是小有名氣。它自鳩摩羅什於 402 -412 年間譯出後,在短短的數年間,《高僧傳》<亡身篇>中的釋法進,在北涼沮渠蒙遜時代 (401-433) 即誦持《金剛經》。[40] 又宋齊時代的釋慧基 (412-196) 也是「善誦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般若、勝鬘等經」。[41] 該《金剛經》一譯出就被採用,可見羅什在當時的譯經名聲應該是被肯定的。
另一則相似於「經師」的「誦經」者 - 釋法宗,「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母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舔子,宗迺悔悟」,因此「摧弓折矢出家業道」,而且「蔬苦六時以悔先罪」,又「誦法華維摩」。在度眾方面,他「常昇臺諷詠」,名聲是「響聞四遠」,並且「士庶秉其歸戒者三千餘人」,因而「開拓所住以為精舍」,該精舍「因」以「誦」持「為」其「目」的,故號曰「法華臺」。[42] 從上述傳文中得知法宗以「誦法華、維摩」為其修持的依據,後來由於「諷詠」經典而聞名,而其「精舍」亦以誦經的方式度眾,傳文中並未提及他有「轉讀」或「梵唄」之事,僅言「諷詠」,因此筆者推測此乃慧皎將其列入「誦經」篇之故吧。 事實上,「諷詠」與「梵唄」似乎很難劃分界線,慧皎在 <經師> 篇的評論中提及:「詠經則稱
註37:該本為高雄縣大樹鄉「光雲寺」所持用。
註38:該本為台南市「竹溪寺」的用本。
註39:見T.14/446, P.364; T.20/1161, PP.663c, 664a.
註40:T.50/2059, P.379a.
註41:T.50/2059, P.404b.
註42:T.50/2059, P.407a.
頁82
為轉讀,歌讚則號為梵唄」,[43] 至於其中的差異,本文將於下一節 「經師」篇中再論述。
「誦經」是否是一個極佳的修持法門,慧皎對此評論如下:
「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總持難得,惛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遂通神於石塢....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啟。....獨處閑房,吟諷經典.. 足使幽靈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詠)誦法言,以此為音樂者也。」[44]
慧皎很明白的承認諷誦的利益很大,但由於執持一念於經文,容易惛沉,故真正成究者並不多,此諷誦法語也是聖賢所讚美的。由於「總持」-- 集中精神於一念,而實際的德行內蘊,表徵於外的感應就隨而出現,可見誦經對修持有其正面的功效。[45] 不僅如此,它亦可振奮心靈,當作音樂以陶冶心情。故誦經有多層的益處,無怪乎慧皎特設「誦經」一科,應別有目的吧。 事實上,誦經、禮懺也是入三昧的前方便,天台智者大師於《法華三昧懺儀》中提及:
「先自調伏其心,息諸緣事.... 生重慚愧,禮佛懺悔,行道誦經坐禪觀行,發願專精,為令正行三昧,身心清淨無障閡故,心所願求,希克果故」。[46]
行者先息滅妄想,調伏自心,再以慚愧心禮懺,並藉誦經而令心專注,進而入禪觀,由於「專精 - 專注」而入三昧 (samadhi 定),此禮誦即是入道的前方便法門,也難怪慧皎讚歎禮誦的功效大。
二、經師科
除了「誦經」之外,慧絞又增設了以誦經度眾的「經師」篇,該篇收有正傳 11 人,附件 20 人,大都以「轉讀」、「音聲梵唄」而著稱,也許稱之為「轉讀經師」會更貼切些。 「轉讀」有二義,一謂「詠經則稱為轉
註43:T.50/2059, P.415b
註44:T.50/2059, P.409a.
註45:總持是梵語陀羅尼之義譯,能持,集種種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亦謂持善不失,持惡不生;見《翻譯名義集》,T.54/2131, P.1131b.
註46:T.46/1941, P.949c. 有關誦經見另一文,大野榮人,〈天台智顗 誦經觀〉,《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2-1, 1983, PP.255-260.
頁83
讀」,二則「僅讀每卷經之初中後數行亦曰轉讀,謂轉翻經卷而讀也」。[47] 由於以諷詠或詠歌的方式輾轉讀誦經典,故音聲梵唄因之而起。
在該傳中最早的轉讀經師是帛法橋,「少樂轉讀而乏聲」,因而「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直到第七日覺得「喉內豁然」,於是作「三契經」,「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年至九十聲猶不變,晉穆帝永和年間 (345-356) 卒」。[48] 由於絕食禮懺觀音菩薩而得到至死音聲不變的感應,此乃由於轉讀經典而契入修行的另一典範。 此「三契經」到底是什麼?在《僧祐錄》與其它的經錄中未有「三契經」的記錄,很可能它只是轉讀歌詠中,聲韻節拍的三轉韻。 在《翻譯名義集》中提及:
「梵唄....唄者短偈以流頌...契之一字,猶言一節一科也。弘明集頌經三契,道安法師集契梵音」[49]
可見「契」是指諷詠經典偈頌的一節、一科或一段。 另在《南海寄歸傳》(691 義淨撰) 亦提:「所誦之經多誦三啟,乃是尊者馬鳴之所集置,...取經意而讚歎..次述正經...迴向發願,節段三開,故云三啟。」[50] 可見三啟即是讚歎 、誦經與迴向發願,此乃諷詠經典的三個步驟,同理推之,三契也應該是梵唄中諷頌的三個節或段。
慧絞於該科中所列的 11 名轉讀經師,大都是對轉讀、經唄有特殊貢獻者,並時而受到皇帝貴族的敬重。 例如正傳中的支曇籥即是個異人,晉孝武帝 (362-396)「從其受五戒,敬以師禮」,又「所製六言梵唄傳于後」。其弟子法平、法等二兄弟 (元嘉末年 453 卒) 因轉讀經卷而稱名,甚至被讚歎他的讀經不亞於他人講經,「嚴除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51]
另有一種在夜半高聲轉讀,令行者開神醒悟的「一語驚醒夢中人」方式,即是釋智宗 (429-459) 之例,他善「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至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眾低昂睡(蛇)地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
註47:《中文大辭典》,No.8, P.1764. 聽說現代有些經懺師,為亡者或信眾誦經時,為了節省時間,只選每部經的初、中、後數頁誦之,這也許是淵源於此「轉讀」的儀式吧。
註48:T.50/2059, P.413b.
註49:T.54/2131, P.1123c.
註50:T.54/2125, P.227a.
註51:T.50/2059, P.413c.
頁84
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 這種在夜闌人靜突如其來的聲響與法語,的確會振奮人心,激起道心,無怪乎此讀經方式會一時受到欣賞。 在智宗之後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他們二人轉讀誦經的方式與智宗相似 --- 聲音洪亮,讀誦的內容不取之於他人。而道詮的方式卻「逢時的」受到宋明帝 (在位八年 465-472) 的欣賞而盛行一時,如傳文述:「宋明 (帝) 忽賞道詮,議者謂逢時也」,[52] 可見當時的「經師」也有不同的應世伎倆。
在智宗的傳文中「八關」應該是當今佛教界流行的「八關齋戒」,六朝時代由於種種齋法的流行,「八關齋」也應是當時的潮流之一。 早在姚秦時代 (378) 竺佛念所譯的《鼻奈耶》已提及「行八關齋」之事,[53] 又曇無讖約於426 - 428年間所譯的《優婆塞戒經》卷五中的 <八戒齋品> 亦詳述受「八戒齋」的功德,[54] 可見在第四世紀中國佛教已有「八關齋戒」的觀念。 再者,據《僧祐錄》卷四「失譯 - 新集所得,今並有其本」中有「八關齋經一卷」的記錄。[55] 又卷十二 <法苑雜緣原始集> 中有:「八關齋緣記」、「皇帝後堂八關齋造十種燈記」的記錄。[56] 連皇帝都會為八關齋而造燈,可見「八關」的法會,在南北朝時代是被重視的,而現今的「八關齋戒」法會也應是淵源於當時了。
另一位為宋孝武帝所讚歎的是釋曇遷 (384-482),傳文述之「篤好玄儒」、「游心佛義」又「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不僅如此,也「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可真是儒釋道皆通的才子。他又與當時的名門有來往,如彭城王劉義康、范曄、王曇首等。[57] 然他又不畏權勢而正義的為其好友送葬,當范曄被誅無人敢接近時,[58] 曇遷卻「抽貨衣物」且「悉營葬送」,因此感動「孝武聞而歎賞」並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註52:T.50/2059, P.414a. 中宵即是中夜,亦夜半之義,見《中文大辭典》,No.1, P.417a.
註53:T.24/1464, P869b.
註54:T.24/1488, P.1063a.
註55:T.55/2145, P.30b
註56:T.55/2145, PP.91a,93a
註57:彭城王劉義康與王曇首都與佛教人士有往來,其傳記見梁沈約,《宋書》,台北:鼎文書局,1990, PP.1789-1796, 1678-1680.
註58:范曄被誅一事,見《宋書》, P.1819.
頁85
能為宋孝武帝所讚賞,又被列入宋史,其德行該非等賢之輩了。[59]
宋孝武帝不僅賞識釋曇遷,也器重經師釋曇智 (409-487)。 曇智「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而他的轉讀技術是「獨拔新異,高調清徹」,曾為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人「深加識重」。[60] 此外,南齊文宣王蕭子良亦重視轉讀沙門釋僧辯 (卒於 493),他的讀經風格是「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傳文述文宣王於 489 年「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便覺醒至佛前詠「古維摩一契」,次日召集「善聲沙門」多位一起作「經唄」,僧辯即奉命作「古維摩一契」與「瑞應七言偈一契」,此二契可說是最聞名者,如文述「最是命家之作」,可惜後來「訛漏失其大體」了。
另一奇人釋曇憑,對於轉讀的音調甚為用心,少時自認超群但未被世人認同,如傳文述:「音調甚工而過旦自認,時人未之推也」。於是他更「專精規矩」、「更加研習」, 終於晚年「出群」。他不僅轉讀漢音,且諷誦梵音,其梵音一吐「輒鳥馬悲鳴,行途住足」,可見其轉讀之功力足以感動飛禽走獸。他又製造銅鐘,願未來有「八音四辯」,[61] 「庸蜀有銅鐘始於此」。[62]
由上述的轉讀經師中得知,由於帝王的護持,轉讀的風氣大盛於宋、齊間。 事實上,當時有名的轉讀經師,並非德行都是高超者,慧絞另列八人且明白的表示這些都是在齊代的轉讀名人,但僅出名於「詠歌」,並無特殊的「高譽」,故不足以記傳。如文云:
「釋法鄰、曇辯、慧念、曇幹、曇進、慧超、道首、曇調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荊陜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63]
註59:T.50/2059, P.414a
註60:T.50/2059, P.414b. 蕭思話是孝懿皇后的弟子,其傳記見《宋書》, PP.2011-18. 王僧虔是王曇首之子,其傳記見蕭子顯,《南齊書》,台北:鼎文書局,1990, PP.591-5.
註61:八音:極好音、柔軟音、和適音、尊慧音、不女音、不誤音、深遠音、不竭音,四辯:義辯、法辯、辭辯、說辯。見《三藏法數》,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86, PP.330c,444c.
註62:銅鐘始於三國時的《魏志》,《晉書》亦載晉安帝時「霍山崩出銅鐘六枚」,《宋書》亦載漢中城固縣水際,岸崩得銅鐘十二枚。見《中文大辭典》,No.9, P.704. 可見早在第三世紀中國已有銅鐘,但湖北與四川省同銅鐘的使用使於曇憑。因為庸國,在春秋時被楚滅的一國,故城在今湖北省竹山縣東南。又蜀即是今四川省成都市。《中文大辭典》,No3, P.1282c, No8, P,396a.
註63:T.50/2059, P.414c.
頁86
慧絞對該科亦作評論,首先解釋「詠歌」與「經唄」的淵源,其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詠(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 在中國的習俗中對言語難以表達者即以歌詠之,而印度則是以偈頌來唱贊;在評論中慧絞也點出經唄之源流:「如億耳細聲於宵夜」。[64] 億耳的典故出於《十誦律》(404 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卷二十五,佛讚億耳:「汝善讚法,汝能以阿槃地語聲讚誦,了了清淨盡易解。」[65] 據《大宋僧史略》的記載,億耳 (Sona-kotikanna) 即是最早使用讚誦者:
「讚唄原始,案十誦律中,俱胝耳 (即億耳)作三契聲以讚佛,其人善唄易了解。」[66]
慧絞云:「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號為梵唄」,[67] 「梵唄」,梵語 Bhaasa (般遮), 在漢譯佛典詮釋上,有以曲調來誦經、讚詠、歌頌佛德,並含有讚歎、止斷之意,即是「外緣已止已斷,爾時寂靜,任為法事」。[68] 然而在梵文的原意上,Bhaasa 則有「light, lustre, brightness (光明、光彩、亮麗)」,也有「of a dramatic poet (戲劇化詩人的)」,它的語詞變化 Bhaasaka 就有「causing to appear, enlightening, making evident or intelligible (引起出現,覺悟,使印證,使成有才智的)」之意。[69] 可見 Bhaasa 有誦詩、光亮、悟道之意,然漢譯佛典卻綜合其意,而有歌讚佛德,使心清靜、導至悟道的詮釋。經由梵唄的唱詠而契入佛道,故梵唄也應是修行法門之一了。
更進一步,慧絞對梵音與漢語再分析:
「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70]
註64:T.50/2059, PP.414c-415a. 在宮本藏經中「詠」即「韻」。
註65:T.23/1435, P.181b. 阿槃地即Avanti,亦譯阿槃提、阿槃陀、阿和提、阿般提﹍等,見赤沼智善,《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京都:法藏館,1931, PP.66-68。Avanti 國在佛陀時代是十六大國之一,其首都是 Ujjayinii ,在古印度時它位於 Kau`saambii 的西方,即是現今的Malwa 區域。見 Japanese-English Buddhist Dictionary, Tokyo: Daito Shuppansha, 1965, P.4.
註66:T.54/2126, P.242b.
註67:T.50/2059, P.415b.
註68:T.54/2131, 《翻譯名義集》, P.1123c.
註69:Monier 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Delhi, 1990, P.756a.
註70:T.50/2059, P.415a.
頁87
此已明顯的道出梵音不傳之因,乃由於複音與單音之故了。 不僅如此,慧絞亦提到聽唄有五利 --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 慧絞所提的五利說,由於詞句完全相同,故可能引自於《十誦律》(404譯),該律本云:
「有比丘名跋提,於唄中第一,是比丘聲好,白佛言,世尊,願聽我作聲唄,佛言,聽汝作聲唄,唄有五利益,...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聞唄聲,心則歡喜」。[71]
此五利說也許緣於梵音的五種清淨,在《長阿含經》卷五,梵童子告忉利天曰:
「其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何等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徹,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其音周遍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72]
聽了此清淨的梵聲,身心寧靜,當然身體就不易疲倦,心也會受其薰陶而精進不懈倦,對於正法即能善思惟而能憶持不忘,又受清淨梵音的薰習自然音聲就會漸佳,如此的持續用功乃至証道,諸天就會歡喜,難怪聽梵唄有此五種利益。
中國的梵唄始於魏陳思王曹植,慧絞述「梵唄之起亦兆自陳思」,由於「深愛聲律,屬意經音」,又曾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響,乃配合漢曲製成梵唄,而刪治太子瑞應本起經,作四十二契之聲明。[73] 慧絞再述梵唄的流傳過程:
「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而不存,...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曰泥洹唄。爰至晉世,有高座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74]
曹植之後,又有支謙所傳的梵唄三契,可惜已佚失。依《高僧傳》中的【康僧會】傳云:「謙...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提連句梵唄三契。」[75] 可見支
註71:T.23/1435, P.269c.
註72:T.1/1, P.35bc.
註73:T.50/2059, P.415a, T.52/2103,《廣弘明集》, P.119b.〈太子瑞應本起經〉收於 T.3/185, P.472, 吳 (222-228) 支謙譯,述釋尊修行與成道等事,為佛教的重要文獻。
註74:T.50/2059, P.415bc.
註75:T.50/2059, P.325b.
頁88
謙的梵唄三契是依無量壽經而製。 繼而康僧會亦造「泥洹梵唄」,此仍存於梁代,且出自「雙卷泥洹」,此即二卷的泥洹經。 在《僧祐錄》的「新集異出經錄」中記載:
「般泥洹經 支讖出胡般泥洹經一卷,支謙出大般泥洹經二卷,竺法護出方等泥洹經二卷,曇摩讖出大般泥洹經三十六卷,釋法顯出大般泥洹經六卷、方等泥洹經二卷,釋智猛出泥洹經二十卷,求那跋陀羅出泥洹經 一 (= 二) 卷...右一經,七人異出,其支謙大般泥洹,與方等泥洹大同,曇摩讖涅槃,與法顯泥洹大同,其餘三部並闕,未祥同異」[76]
二卷泥洹經的譯者有四人:支謙、竺法護、釋法顯與求那跋陀羅。康僧會是三國時代的吳赤烏十年 (247 A.D.) 抵建業,在他之前有支謙,亦於 223 年間至漢境譯經。在孫權所統制的吳國偏居江左,其佛教的流傳誠如《高僧傳》中的【康僧會】傳云:
「時孫權所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支謙...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吳赤烏十年 (247 A.D.) 抵建業。」[77]
可見支讖、支亮、支謙先後抵達吳國之後,康僧會亦至江左弘法。 竺法護則 (Dharmarak.sa) 是於西晉武帝之世 (265-289) 至西域,沿路傳譯大小乘經凡 149 部,於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後值惠帝西幸長安,護與門徒遷席,至昆池遘疾卒,春秋七十有八。[78] 另求那跋陀羅 (Gunabhadra) 也於晉元嘉十二年 (435) 抵廣州。[79] 再者,釋法顯所譯的「二卷方等泥洹經」亦是在他由印度返國之後,在京師與佛陀跋陀於東晉義熙年間 (405-418)所譯。[80] 故以上三位譯者在時間上都比康僧會晚。 一則由於時間上相近,二則又由於都是地處江左的吳國,故康僧會的泥洹唄所依的「雙卷泥洹」,
註76:T.55/2145, P.14a.
註77:T.50/2059, 「譯經」篇中「康僧會」傳文,P.325a.
註78:據最早的【竺法護傳】載於《僧祐錄》,T.55/2145, 是「譯149部」,見 PP.97c-98a。但《高僧傳》T.50/2059,云:「譯165部經」, P.326c。在這二部傳記中均提他於晉惠帝年間 (290-306) 避居而卒,應非陳援庵,《釋氏疑年錄》所依《開元錄》的記載「晉建興末卒(316)」,收於《現代佛學大系》NO.3,台北:彌勒出版社,1982, P.1.
註79:依最早的【求那跋陀羅傳】,於《僧祐錄》T.55/2145, P.105c.
註80:見【釋法顯】傳,於梁僧傳, T.50/2059, PP.337-8.
頁89
應該是支謙所譯的二卷泥洹經的譯本。
又如慧絞所述梵唄流傳至晉世,有位高座法師初傳「覓歷」。此高座法師的事蹟記載於《僧祐錄》的【尸梨蜜】傳中:
「尸梨蜜 (`sriimitra),西域人也,時人呼之為高座...永嘉中(307-312)始到此土....蜜善持咒術....初江東未有咒法,蜜傳出孔雀王諸神咒,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年八十餘,咸康中 (335-342)卒。」[81]
可見高座法師的「覓歷高聲梵唄」,在梁時仍流傳著。《僧祐錄》的<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 收有「覓歷高聲梵記第十一 -- 唄出須賴經」。[82] 可見覓歷梵唄是淵源於《須賴經》,該經敘述天人為貧者須賴的堅固志心、奉法持戒而「般遮、進歌」。[83]
《須賴經》現存二譯本,均收於大正藏第十二冊,一是 No.328 曹魏甘露三年 (258) 白延譯,另一是 No.329 前梁咸安三年 (373) 支施崙譯。[84] 該經尚有多譯,如支謙於吳黃武年間 (222-229) 也譯了一卷的《須賴經》,或名《須賴菩薩經》,與白延的譯本是同本異譯。[85] 《開元釋教錄》卷四云:
「前梁 支施崙,須賴經一卷,與曹魏白延、吳支謙、宋功德賢所出須賴經同本,見經後記,第三出,咸安三年出。」[86]
該錄於卷十四記載:
「須賴經一卷 曹魏白延- 第一譯。吳支謙 - 第二譯。貧子須
註81:據 T.55/2145, PP.98c-99a,與T.50/2059, 【帛尸梨蜜多羅】傳記,PP.327c-328b。又晉於咸康年間曾造「高座寺」,本名「尸梨密寺」,又因地有甘露井,故亦名「甘露寺」。「西域沙門尸梨密常在石子岡東面,行頭陀,卒葬於此,成帝懷其風素,於塚樹剎。」由此可見他德行的高超,見劉世珩《南朝寺考》,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P.9.
註82:T.55/2145, P.92b.據《僧祐錄》所收一文「覓歷高聲梵記」,筆者懷疑「覓歷」可能是一種梵唄的名稱,而非人名,在高座法師的傳文提及:「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筆者認為應解讀為傳授弟子們一種覓歷高聲梵唄,但仍無可靠的資料證明,故仍持保留的看法。
註83:T.12/328, PP.52b-57a.
註84:見《昭和法寶總目錄》No.1, P.239b.
註85:T.55/2145, P6c. T.55/2146, P.117c.
註86:T.55/2154, P.519a.
頁90
賴經一卷,宋求那跋陀羅 (Gu.nabhadra 或功德賢) - 第四譯又三經同本前後四譯,一存三闕。」[87]
依《開元錄》的記載《須賴經》只有四譯,但據不同經錄的記載似乎不止如此。 好像竺法護也譯此經,《僧祐錄》卷九載:「護公出須賴經」,但其他經錄並未有竺法護譯此經的記錄。[88] 又《大周刊定眾經目錄》亦提:「須賴經一卷,高貴鄉公譯。」[89] 可見《須賴經》前後可能有六譯:白延、支謙、竺法護、支施崙、求那跋陀羅、高貴鄉公等。[90] 依高座法師的年代推敲,其所依之《須賴經》應該有可能是支謙、白延或竺法護的譯本,其他的譯本時間上大都晚於高座的圓寂。
此外,慧絞還提及當時所流行不同音韻的梵唄,如支曇籥製的「六言梵唄」,也有不知作者的「西涼州唄」,並挽惜這些梵唄原是出自名師,但已失傳,只有孩童私自傳誦,已無一定的規矩,因為都是「音聲梵唄」,所以慧絞列入該科之末,並言:
「籥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授,疇昔成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91]
慧絞很清楚、很有次第的介紹「詠歌、梵唄」的流傳始自曹植,經由支謙、康僧會、尸梨蜜高座法師、支曇籥乃至宋、齊、梁年間仍流行著。
不僅慧絞清楚的介紹梵唄的流傳因緣,更早的僧祐亦於《僧祐錄》的<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 中感歎經唄導師在南朝倍受尊崇,以致晚進僧眾盲目跟從,以為它是必習的法門,而不知其根源,如序文云:「新進晚習專志於轉讀,遂令法門常務,月修而莫識其源,僧眾恆儀,日用而不知
註87:T.55/2154, P.631a. Gunabhadra 亦名功德賢,見《昭和法寶總目錄》No.1, P.664a.
註88:T.55/2145, P.62b.
註89:T.55/2153, P.444c.
註90:依時間先後推算,支謙本 (222-229) 應是第一譯,白延本 (258) 即是第二譯,竺法護本可能於元康七年 (297) 前後譯,見 T.55/2145, P.62b,可能是第三譯。支施崙本 (373) 也許就是第四本,求那跋陀羅本 (435-443) 年間譯,即是第五譯,高貴鄉公譯本無年代的記錄,也只出現一次在《大周錄》中,並無在其他經錄中記載,也許暫列為第六譯。
註91:T.50/2059, P.415c.
頁91
其始,不亦甚(奇怪、過份)乎」。 於是他就「檢閱事緣,討其根本...辯始以驗末,明古以證今」的「記錄舊事以彰勝緣,條例叢雜,故謂之法苑。」 此 <法苑> 的【經唄導師集】中有 21 首有關梵唄、法樂梵舞、讀經道人名并銘和轉經記...等的記錄。 雖然婉惜新進的盲目跟從不知其源,但僧祐亦讚嘆經唄的功效:
「經唄導師之集,龍花聖僧之會,菩薩秉戒之法,止惡興善之教、或制起帝皇,或功積黎庶,並八正基跡,十力逵路,雖事寄形跡,而勳遍空界,宋齊之隆實弘斯法,大梁受命導冠百王,神教傍通,慧化冥被,自幼屆老,備觀三代,常願一乘寶訓與天地而彌新。」[92]
很顯然地,由此【經唄導師之集本】得知,僧祐是讚嘆「經唄導師」有化俗的功效,也認為該集是帝王與聖僧的文教之會,是菩薩道的秉持之法,更是止惡行善的法門。經唄的製作雖起於帝王,而功勞績效顯於百姓。他也以「八正道」與佛的「十力」,來表達佛法的教門,也讚賞佛法有遍滿虛空的無形功勳。他更認為宋齊佛教之興隆實因弘揚經唄之故,而佛教在梁朝已是登峰造極的包容、感化其他的神教。僧祐又自云跨越宋、齊、梁三代,常希望一乘佛法能歷久而彌新。 這 21 篇的文集中就有陳思王、齊文帝、竟陵文宣王等 7 篇王族的文記,可見「經導」在南朝是非比尋常的倍受帝王的重視。也難怪《梁僧傳》特設「經師」一科,該科中的支曇籥、智宗、曇遷、曇智乃至僧辯,均受帝王與皇族的敬重與賞識,南齊文宣王蕭子良更作「經唄新聲」,如此不難揣測「經導」在宋、齊、梁間已不分權位的高下而蔚成時尚,其普及性是上至皇宮貴族下至平凡百姓了。 又這 21 篇梵記中齊代的竟陵文宣王、齊文帝就有 6篇 ,幾乎佔了三分之一, 故在南朝中「經唄」流行的最高峰應非齊代莫屬了,這也許是竟陵王蕭子良熱衷此道之故吧。
三、唱導科
該科收有正傳 10人,附屬 7 人也都以「宣唱」聞名。 這十個傳文中大都有個共通點 - 齋會、懺悔、唱導,這三項幾乎都進行於齋會中,首先禮懺,接著即是「宣唱化導」,如此地一一在齋會中進行。 唱導並非佛家的專有名詞,在《說文解字》曾解:「唱,導也,眾口昌聲」,「唱而引導
註92:T.55/2145, PP.90-92.
頁92
之,引申則有首作某項主張義」。 再者,《後漢書》、《三國志.魏志》中的傳記也提及這個名詞。[93] 此外,在佛教方面,羅什譯的《妙法蓮華經》<踊出品> 中也採用「唱導」之詞:「菩薩眾中有四導師....是四菩薩於其眾中,最為上首,唱導之師」; 又此段在隋本《添品妙法蓮華經》中也幾乎是相同的譯文;然西晉竺法護《正法華經》卻無此名詞的出現。[94]
唱導的儀禮非出自中國,它有其印度之淵源,據《大宋僧史略》:
「唱導者始則西域,上座凡赴請,咒願曰,二足常安,四足亦安,一切時中皆吉祥等,以悅可檀越之心也。舍利弗多辯才,曾作上座,讚導頗佳,白衣大歡喜,此為表白之椎輪。」[95]
可見唱導即是耆宿大德應邀受供時,需為檀越 (齋主) 祈求吉祥,此祈求文即是咒願,以讚歎、宣唱的方式表達,也稱唱導,也有表白之意 - 說明某情形。唱導之人亦稱「導師」,導師也有二義,據《大宋僧史略》:「導師之名而含二義,若法華經中,商人白導師,言此即引路指述也;若唱導之師,此即表白也。」[96] 因此唱導之師的作用,即是表白某事。《釋氏要覽》亦云:「表白,僧史略云,亦曰唱導也。」[97] 可見「唱導」即是「表白」。
此外,對佛法的諷誦吟詠是釋迦佛所聽許的,其典故出自《根本說一切有部毘柰耶雜事》(唐 710 義淨譯),卷四記載善和比丘聲好的因緣,善和比丘的過去生是隻能鳴鳥,由於見迦葉佛的莊嚴而「繞佛出妙音響」,「感得好聲響徹梵天,令人愛樂」,其音聲「美妙最為第一」,但在彼佛時雖修梵行而無所證獲,直到釋迦佛時代才證阿羅漢果,「於弟子中唱導之師說為第一」,因此「佛許二事作吟詠聲,讚佛德、誦三啟」。[98] 另該律本亦載:「送喪苾芻可令能者誦三啟無常經,並說伽他 (gaathaa 偈頌)為其咒願。」[99] 可見諷誦吟詠經典也是來自印度的習俗。
本科傳文中,首先是獨步宋代之初的釋道照 (368-433) 年六十六,平
註93:見《中文大辭典》NO.2, P.824c.
註94:T.9/262, P.40a, T.9/264, P.174b, T.9/263, P.110c.
註95:T.54/2126, P.242a. 咒院即唸誦迴施,為施主做種種讚嘆咒願,見 T.54/2126, P.276b.
註96:T.54/2126, P.244c
註97:T.54/2127, P.276b.
註98:T.24/1451, P.223a.b.
註99:T.24/1451, P.287a.
頁93
西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又「披覽群典,以宣唱為業」。[100] 可見他是博學多聞、精通經、史,並以唱導為度眾的方法。其唱導的特色是「指事適時,言不孤發」,即是他對事情能把握恰當的時機,適時給于機會教育,因此他能表現優異的「獨步於宋代之初」。 宋武帝曾於內殿設齋,則請道照為唱導師,道照略述人生「百年,迅速遷滅」,「苦樂參差必由因 (召)果」,如此的感動武帝而賞賜他「三萬」錢。又臨川王道規依他而受五戒,尊奉它他為師。
唱導的另一特色即是「善誘」,此即釋曇穎的例子,曇穎,會稽人,年八十二,傳文云:「誦經十餘萬言... 性恭儉,唯以善誘為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顯然地,曇穎的個性是謙恭又勤儉,擅長於誘導眾生,故獨鐘於唱導,又其此技似乎是天賦且獨具風格。此外,他也有平等心,不為權勢名利而宣唱,只要禮請,不論貧富貴賤,均為赴約,如文曰:「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101]
博學、善誘之外,「出口成章」也是成為優異唱導師的必備條件。釋慧璩,丹陽人,宋大明末卒,年七十二,他「讀覽經論、涉獵書史,眾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可見他不僅是博學多聞,也是個有天賦的唱導師,能臨機應變的出口成章。宋孝武帝設齋,慧璩受請唱導,帝悅賞錢一萬,後為「京邑都維那」。 另一位亦受孝武帝賞賜的是釋曇宗,也是「博通眾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的唱導師,遺留著作 <京師塔寺記> 二卷,[102] 可見他不僅博學,唱說的功夫技巧也獨特,更能著書論說。
再者,釋曇光,會稽人,年六十五,「迴心習唱,製造懺文」,亦為宋明帝稱讚並賜「三衣瓶缽」的唱導師。 另外,釋道儒 (410-490)、釋慧重
註100:道照圓寂的年代,據藏經高麗本云元嘉三十年 (453) 卒,但宋、元、明三本以元嘉十年 (433) 卒,本文依《釋氏疑年錄》,採宋、元、明三本之說法卒於433年,P.12。尺牘,「亦名書牘,凡筆跡文辭皆得,謂之尺牘」,見《中文大辭典》No3, P.763a. 道照的傳文見 T.50/2059, P.415c.
註101:見其傳文 T.50/2059, P.415c.
註102:此二卷的塔寺記,不同於大正藏第51冊所收的《寺塔記》一卷,與《梁京寺記》一卷,可能已失佚了。
頁94
(415-487) 都是宋末齊初的唱導名人。[103] 從這些實例中得知,當時的唱導師大都是博學與善巧,有的還「善神咒」為人醫病,且「所治必驗」,此即釋慧芬 (407-485) 的例子,他「學業優深,苦行精峻」,在齋會中常為大眾說法,於「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為了修道而於北魏廢佛時,逃往南方。對於戒律則是「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難) 虧節」,也留有 <訓誡遺文> 等。[104]
此外,釋法願、法鏡師徒也是奇特的唱導師。 師法願 (414-500) 年八十七,「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耆父占相,皆備盡其妙」,並教導宋太祖「陰陽秘術」。他以靈驗的占卜相術受帝王朝臣的重視,也因向刺史建議「欲減眾僧床腳,令依八指之制」,而遭禍害。[105] 此乃因「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106] 於是「致聞孝武,即敕願還都」。武帝問願「何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因此「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法願仍堅持菜食,而「不迴其操」。如此則「帝大怒,敕罷道」的下令迫其還俗,並命他為「廣武將軍」直守華林佛殿。雖然被罷還俗「形同俗人」,但他仍然「栖心禪戒,未嘗虧節」。因此在武帝駕奔之後,他就時來運轉的受昭太后「令聽還道」。 對於不測之事能料事如神的法願,也受齊太祖高帝、世祖武帝「事以師禮」。不僅如此,文惠太子、「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希遵師禮」。法願受王公、貴族、百姓的敬重,其財富亦隨之而來,他「隨以修福,未嘗蓄聚」。他的修福方式很奇特,除了收購米穀餵食魚鳥、採買飲食賑給囚徒之外,竟然還有「雇
註103:T.50/2059, P.416.
註104:T.50/2059, P.416bc. 宋、元、明三本有(+終難)等字,意思更完整。
註105:依戒律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的床腳不得超過八指。比丘戒見《十誦律》,弗若多羅共羅什404年譯:「若比丘過八指作床腳者,應截腳入」, T.23/1435, P.127c. 比丘尼戒見《摩訶僧祇律》T.22/1425, P.538b. 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律條見《四分律》T.22/1428, P.693b.
註106:釋僧導的傳記亦載於《高僧傳》卷七〈義解篇〉,T.50/2059, P.371a-c. 傳文中敘述僧導 (春秋96) 曾為羅什的譯經「參議詳定」,並「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且對滅佛逃難的數百沙門,「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為之流涕哀慟。」亦與孝武帝有往來,言「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砂石瓦礫,便為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由此可見,僧導是博學多才、護教衛法,深受孝武帝的器重。當法願提議「八指之制」時,也許僧導不贊同,而上奏孝武帝,乃致法願受害。此二人的作風不同,一是重義學,一是重秘術與唱導,也難怪會有思想歧見。又慧皎把二人均列入「高僧」中,可見各有其特色,致於他們個人的德行,是見仁見智的,筆者不予置評。
頁95
人禮佛」、「借人持齋」的善巧菩薩行。 因此慧皎褒言他的「興功立德,數不可紀」,但也率然直言的貶其唱導術是「善唱導及依經說法」,但是「率自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為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即是批評他只重視適合時機,而罔顧音韻、直心而出,以致言語雜亂,可說是愚昧之行。 然傳文之末卻也提及一事,以表示他尊佛護寺的衛教精神。 有一次,他入定三天,「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籮矣」,原來是寺旁的三面房屋遭火焚毀,弟子勸其出寺,但他說「佛若被燒,我何用活」,誓死保護佛寺,結果「唯寺不燼」。
慧皎以不小的篇幅來敘述法願的事蹟,這也是十個唱導師中最長的一篇傳文。也許因法願影響的層面上至帝王,下至庶民,又時間上是從宋太祖(就位 424) 至齊武帝 (卒 493),歷經二個朝代、七個帝王。他從得寵到被敕還俗,又再次的得寵敬重以致於名利雙得,他嚐盡了人生的榮、辱、興、衰,竟然還能「雇人禮佛」、「借人持齋」,以金錢善巧方便的引導眾生,此非「各各為人悉檀」的菩薩行嗎 ?[107] 傳文中並未提及他有博覽經論的深厚文字基礎,也難怪他的唱導文詞被批評是雜亂的, 又他以契眾生的根機為要,並以占卜相術而聞名,可見他是另一型的異人,吾人實難以正常的尺來衡量他。
法願的弟子法鏡 (437-500), 年六十四, 承其師業「研習唱導」,其唱導技術亦很優異的「有邁終古」,因此受「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他很有平等心「不拘貴賤,有請必行」,也「常興福業」的修福結緣,其個性「敦美」。他的學識基礎也許不佳,故傳文云「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經論義學的深度不夠,但有自然領悟的天賦。 可見法鏡與其師法願大致相同,不重視義學,只順乎自然,秉天賦而宣唱法理。
從以上僧傳所舉的十個例子中得知,唱導師大都分為二種,一是博通經論出語成章,又能善巧誘引眾生,博得帝王、大臣的敬重。二是先以靈異的占卜術或咒術攝眾,再以佛法宣導。 總之,不論先以博學或是咒術攝受人,都是「先以欲勾遷,後令入佛智」的善巧方便法門,只要導入正
註107:見《大智度論》T.25/1509, P.59b.悉檀,梵語 Siddhaanta
頁96
法,引人向善,即是優良的唱導師,無怪乎慧皎將這二類人歸入高僧的行列。
然慧皎對於該科的評論是先給于名詞的詮釋:「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把佛理以宣唱的方式表達出來,以達到教化民心的作用。接著即討論唱導的源流,他說:
「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倡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108]
很顯然的,最早佛法初傳時的集會,即是唱唸佛名而禮拜,也即是類似「禮千佛」的模式 - 一佛一拜。 待禮到中夜疲倦時,則禮請大德說法,此亦相似於現今佛教禮懺、唸佛法會中所穿插的「開示」。 只是現代的開示是以言語表達,而唱導則注重音聲以攝眾心。 如慧皎所云唱導所貴四事: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眾、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 可見此四事的用處是:聲 - 警眾之用,辯 - 適時為用,才 - 則為綺製文藻,博 - 廣博書史資料。 除此四事,「適以人時」也是個重的因素,即是適時、適人的依對象而論,誠如慧皎所言對四種人應有不同的說詞:
一. 對「出家五眾」,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或許認為以無常為警惕則會令僧眾更精進於道業。
二. 對「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僧人的博學與文雅的辭藻,易令高位者生起恭敬心而得度。
三. 對「悠悠凡庶」- 平凡百姓,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百姓講求的是現實的生活,所以直接談及生活週遭所發生的事,容易了解與接受。
四. 對「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此山民野處應指的是山中匪徒,對匪徒則用相近其局面、層次的言詞,明白的陳述罪狀,無須用華麗高雅的詞藻。
進一步的,慧皎更認為若能「知時知眾」,又能口才伶俐的「善說」,則更
註108:T.50/2059, P.417c.
頁96
易「懇切感人、傾誠動物」的感化人類、飛禽走獸等眾生,「此其上也」- 也就是最上等的度眾方式了。[109]
據慧皎的評論,中國佛教中最早昇座唱導的是盧山慧遠 (334-416),論云:「盧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昇高座,躬為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110] 在齋會中慧遠親自領導,先談三世因果,再述齋會的意義,於是形成唱導的規則。 盧山慧遠之後,諸師爭相學習蔚為時尚,才有本傳 <唱導科> 中所列知名的唱導師。 致於早期的唱導是在法會的那一時段中進行呢? 又如何舉行呢? 慧皎亦提:
「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行周(周行),煙蓋停氛,燈惟(帷)靖耀,四眾專心,叉指緘默。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慼則灑淚含酸。於是闔眾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人迫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為用,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稱。」[111]
由引文中得知唱導舉行於八關齋會的初夜,通火光明,出家、在家男女等四眾弟子,一心合掌默禱。此時的唱導師手執香爐,抑揚高聲,口宣法語,似乎是唱做俱佳地令聽聞者身臨:顫慄、恐怖、喜樂、哀傷之境。此時大眾莫不身心投入,五體投地陳哀懺悔,稱唸佛名以悔先罪,直到後夜鐘響才結束。此種唱導法不僅收攝人心,也似乎能令日月星河感動的「星河易轉」,令人傾瀉滿腔哀愁的情緒,更會使人心充滿法義。 因此,慧皎認為唱導最大的作用,即是適和時宜地令人醒悟 (世間的無常法) --「賞悟適時」,而這對於拔除邪見(真實有常的世間)、確立正信 (苦、空、無常、無我的真理),有其一分的功效。
雖然唱導有其正面的功效,但不良的唱導師也會導至負面的影響。慧皎繼而很詳細的提出其缺點:
註109:以上的敘述出自 T.50/2059, P.417c.
註110:T.50/2059, P.417c.
註111:T.50/2059, P.418a.
頁98
「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己)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謬,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唱習(=宜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懺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屈(出) 頭,臨時抽造,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謦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徒)啟齒。施主失應時之福,眾僧乖古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代(伐)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謂耶。」[112]
引文中淋璃盡致的描寫學問不博、經驗不足的唱導師出醜的狀況:借用舊本、音韻不合,紕漏頻出,而有魚目混珠之嫌,又不熟內文無法臨機應變,倒致口吃慌亂,藉整衣輕咳來拖延時間,使聽眾寒心,也令施主失掉應時聽法的福報因緣,更使欲聽法的僧眾歪曲佛法的真義,斷送聞法生善的機會,而徒增戲論的疑惑,也遭受「濫吹」的譏嫌,致使名師也蒙冤,最後慧皎明白的交待,這一類的人非高僧傳中所述的唱導師。 可見《高僧傳》中所列的十名唱導師,絕非泛泛之輩了,而當時確實有不良的唱導師的存在。
由以上唱導師的傳文中得知,唱導不僅流行於宋、齊年間,亦傳至梁朝的王宮貴族。梁簡文帝的 <唱導文> 記載於《廣弘明集》卷十五,該文的內容大都是稱讚佛德、敬禮諸佛、懺悔業障與祈求發願,例如:
「夫十惡緣句易惑心塗 ....各趣百非纏茲四苦...是以如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奉為至尊敬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歸命敬禮五十三佛....六根之滯猶染...庶憑正法拔茲累染,長享百福,永斷六塵,對至無強,惟佛可恃...」[113]
另有十餘首王僧孺作的 <禮佛發願文> 與 <懺悔禮佛文>,其內容也大致相同。[114] 可見唱導、禮佛、懺悔在齋會或法會中是不可或缺的,而唱導文即是法會進行中的唸誦文,此與現今法會中的「疏文」也許有關,或許是它的前身吧。
註112:T.50/2059, P.418a.
註113:T.52/2103, P.205a-c.
註114:T.52/2103, PP.205-207.
頁99
結論
廬山慧遠的 <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中曾提:「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為本。」[115] 可見「諷味遺典」-- 諷誦經典也是修行的三種法門之一。 本文中所探討的三科 --誦經、經師、唱導,即是「諷味遺典」的法門。 在《高僧傳》卷十四的序文,對於「誦經科」,慧皎云:「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此即藉誦持經文而了悟其含意。慧皎繼而又言:「其轉讀宣唱,雖源 (=原) 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116] 轉讀與唱導的流傳淵源還不夠長久,未有實際的功效出現,[117] 但仍有某一類眾生的需要,故言有應機的功勞。 總而言之,這三科「諷味遺典」的法門,由以上的討論得知,在六朝時代其接受的層度 --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不難發現其功效,不論在修行、或度眾方面確實有其不可抹煞的功勞。
繼而「隋文興法,煬帝倍隆,四海輻湊,同歸帝室,至於梵導讚敘,各重家風,聞常一梵,颯然傾耳」。[118] 經過了隋代的興佛,「經導」-- 經師與唱導,已蔚成風氣,各成門戶形成家風。 然到了唐代「經導」則更發展成「專業化」,與道士唱辯以度帝王,文如《續高僧傳》【釋智凱】傳:「佛道雙嚴,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張鼎雄辯難加,自恨聲小,為凱陵架,欲待言了,方肆其術,語次帝德,(張)鼎延其語,凱斜目之,知其度也,乃含笑廣引。」[119] 顯然是佛家的唱導師勝過道士。 可見「經導」隨六朝的流傳,歷經隋代的興法,到唐朝更是大盛,由傳文中諸唱導文卷數的記錄,[120] 不難發現其廣受歡迎、普遍使用的程度了。 此「經導」的興盛可說是「應時契機」的「善巧方便」法門,似乎不應該如同有些學者貶
註115:T.52/2102, P.85b.
註116:T.50/2059, P.419a.
註117:引文中的「原出非遠」有含糊不清之意,亦可解為「非出自(慧)遠」,但在〈唱導科〉的評論中曾述其有印度佛教的背景,但中國則始於廬山慧遠,故筆者認為以「淵源的時間長遠」解之較合理。
註118:T.50/2060, 《續高僧傳》卷三十,〈雜科聲德篇〉【釋慧常】傳文,P.704c.
註119:T.50/2060, P.705b.
註120:唱導師,【釋真觀】著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餘卷,見 T.50/2060, P.703c. 後梁【釋無作】,述諸色禮懺文數十本,注道安六時禮佛文一卷并詩歌,見 T.50/2061, P.897a.
頁100
它為「照顧廣大的低下階層」的方法吧! (May.9,1998 Bodhi Vih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