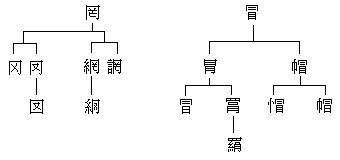*miuaηxmauh管窺
高明道
法光學壇
第四期(2000)
頁40-56

頁40
摘要:
本文以*miuaηxmauh(罔/網冒/帽/■[忙-亡+冒])為例來說明在理解古代文獻用語時因受不同層次變數的影響所發生的某種困難。考查相關語料的範疇以漢文佛藏的印度譯著部分與中國撰述部分為主。經由實例的歸類及剖析,筆者對*miuaηxmauh一詞的構成原則、指涉義涵、出現年代和使用分布提出初步的看法。
頁41
A Look at *miuaηxmauh
Friedrich Grohmann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one of those cases in wh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texts is impeded by both the natural disappearance of words from the living lexicon of a language and the corruption inevitable in the course of long-term textual transmission.
*miuaηxmauh, the term under scrutiny, is introduced by way of the form in which it appears in the editions of Hui-chao's commentary on the Suvar.naprabhaasasuutra. Here, it is already written in such a way that the original pronunciation of the second syllable is no longer recognizable and any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word will lead to rather amusing results. However, this does not imply that the term has been correctly interpreted even when the characters avoided major corruption. That quite the opposite is true is documented in those cases in whic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is not influenced by the choice of characters employed in its written representation.
A complete surve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Buddhist canon revealed that all instances in which *miuaηxmauh occurs in translation -only three-are found in Hsüan-tsang's work. These cases are analyzed, if possible with reference to Indian sources, and so is the usage of the term in native Buddhist literature. As a result, the conclusion is reached that,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reflected in old glosses, modern commentaries, and the rare definition in a dictionary, *miuaηxmauh is a binome with one basic meaning -“confused”.
頁42
古書之難懂難讀,一方面是由於語言的演變使然,因為任何自然語言於不同發展時期在發音、辭彙、句法等等層次上,都呈現各種差別,使得讀者容易感到古文、今語之間有鴻溝。另一方面,一本書展轉手寫傳抄、刊刻印刷,時間愈久,次數愈多,問題就往往相對地增加,所以在古籍的解讀上遇到困難,有時可能跟文獻本身的謬誤有關。這兩種因素常常一併起作用,對通暢的閱讀與輕易的理解產生諸多阻礙。非單中國的文言讀物如此,只要是古代傳下來的文本──希臘的、以色列的、印度的……──,這些足以影響瞭解、欣賞、研究人類文化遺產的問題,都在所難免。當然不可諱言,由於漢字字形的特色,中國的古書比較之下還更加充斥誘人「著相」的陷阱。本文則擬舉漢文佛典上一個小例子,隨筆談談此一發人深省的現象。
繼玄奘、窺基之後發揚慈恩宗唯識學的唐高僧慧沼(西元650-714年)[1]留下了若干著作,包括幾部為契經編纂的注釋書。其中有一部十卷的《〈金光明最勝王經〉疏》較為特別,因為保存完整的中國古德《金光明經》注釋裡只有它以義淨(西元635-713年)新譯的《金光明最勝王經》為說解對象,而不像其他注本[2]詮釋曇無讖(西元385-433年)的譯本。
依近代學者的研究,《金光明經》這部歷史上屢經增添、一時廣為弘傳的重要修多羅,最原始的核心不外乎《懺悔品》的非長行部分。[3]其中有一個偈頌,義淨譯作「親近不善人 及由慳嫉意 貧窮行諂誑 故我造諸惡」。[4]慧沼《疏》上分別解釋它的文字說:「畜積不捨,鄙悋稱『慳』;不耐他榮,妒忌稱『嫉』;為罔羂他,曲順彼意稱『諂』;心懷異謀,矯現有德稱『誑』。」[5]這是根據目前流通最廣的《大正藏》援引的,意思大致易懂,只是「罔羂」二字令人茫然。
照《〈大正新脩大藏經〉勘同目錄》,編入《大正藏》的慧沼《〈金光明最勝王經〉疏》以日本東山寶永三年(約西元1706年)刊、宗教大學收藏本為底本,以日本《聖語藏》宋版九號本及《續
頁43
藏》本為輔本。[6]前二種,筆者無緣目睹;至於《卍續藏》,經查證發現,有疑問的兩個字印作「罔罥」[7]。不過「羂」本同「罥」[8],所以在實質意義上《大正藏》跟《卍續藏》在此沒有差別。「羂」、「罥」都是「■[罪-非+繯]」的後起字。[9]「■[罪-非+繯](羂/罥)」原訓為名詞「罔」[10],但也可以當動詞用[11]。因此,儘管「罔罥(羂/■[罪-非+繯])」未見現代大部頭的工具書[12],依字面上的意義,卻無妨把它理解成「用網捕取」。問題是,如果以「為了用網來捕取他人,就偽裝順從他意」為「諂」釋的解讀,則恐怕不但沒有解除疑惑,反而更加鬧出笑話。
實際上,《〈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的這個「罔羂(罥)」是經過形體訛變[13],背後隱藏著一個罕見的中古漢語語詞。說它訛變,因為原來的寫法是「罔冒」;說它罕見,因為以漢譯佛典為例,據初步的考察,歷代譯師中唯獨玄奘(西元600-664年)曾經用過它,而且機率也極少──在這位著名的三藏法師所翻的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14]大量譯作當中,「罔冒」竟只在三個地方出現。一個屬於經,是六百卷《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初會》裡第三百六十六卷的「是菩薩摩訶薩,假使有來欲害其命,劫奪資財,侵陵妻室,虛誑罔冒,離間親友,麤言罵辱,雜穢嘲誚,或捶或打,或割或截,或為種種不饒益事,於彼有情都無忿恨,唯欲作彼利益安樂」。[15]
另有兩個出處則屬於論,而且現傳本的字形多半已經遭到改動。在《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卷第十三單單是「冒」字換成了「帽」字:「言無誑者,誑云何?答:偽斗[16]偽秤,偽函偽語,於他罔帽、極罔帽、遍罔帽,罔帽業欺弄迷[17]惑,皆名為誑。無如是誑,故名無誑。」[18]《成唯識論》第六卷的情況則混亂多了,「冒」除從「巾」作「帽」之外,還有從「心」作「■[忙-亡+冒]」的,且「罔」進而從「糸」:「云何為諂?為罔他故,矯設異儀,險曲為性;能障不諂、教誨為業。謂諂曲者,為罔冒他,曲順時宜,矯[19]設方便,為取他意,或藏己失[20],不任師友正教誨故。此亦貪、癡一分為體,離二無別諂相用故。」[21]
頁44
漢譯釋典上的「罔冒」例雖然只有上引三則,而且悉數出自玄奘一人之手,但也正因為譯者在佛教史扮演的角色具有分量,所以引來日後偶有愛好唯識的中國學者在自己的作品裡援用其中部分資料。慧沼就是古代例子之一。此外還有唐窺基(西元632-682年)注解、明普泰增修的《〈大乘百法明門論〉解》[22]、唐代華嚴祖師澄觀(西元737-838年)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23]、在宋代研究華嚴與天台的子璿所寫的《〈首楞嚴〉義疏注經》[24]和《〈起信論〉疏筆削記》[25]以及宋法雲編集的《翻譯名義大集》[26]。另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唐僧慧寶為憲宗元和元年(約西元806年)完成的《北山錄》寫注,用「罔冒」來解釋「誷」[27]──,從上下文「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取勝,而世有隱瑕匿疣,飾智寵鄙,盜玄匠之虛譽,祕昏情以自誷」[28]來判斷,還是講誑、諂等煩惱。
至於不是參考玄奘譯本、自由使用「罔冒」的例子,出現的頻率也相當有限。藏經裡最早的資料可能是以護教有名的法琳(西元572-640年)[29]在《破邪論》批評傅奕時所說的:「觀奕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冐闕廷處多,毀辱聖人甚切。」[30]這句話後來在彥悰(西元557-610年)的《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和道宣(西元596-667年)的《廣弘明集》都被援引。[31]道宣還在其他幾部作品裡偶而用到「罔冒」:《〈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的「鄙末之小僧妄參眾首,眉壽之大德奄就下行;以武力為智能,指文華為英彥,如斯罔冐,孰可言哉」、《量處輕重儀》的「私懷賕納託勢,隨情迴換重輕,罔冒僧利,並皆重罪」、《釋門歸敬儀》的「法被權道,情投業理;心形兩位,指月雙筌;或以鄙俗淺度不識分量罔冐入真實為沈俗」、《集神州三寶感通錄》的「代有澆淳,時逢信毀;淳信之侶感淨果而高昇,澆毀之徒受濁報而下沒,斯並無辜起惡,罔[32]冐精靈」以及《續高僧傳》的「初為屋子論議法,立圖著經,外施名教,內搆言引,牽引出入;罔冒聲說,聽言可領,及述茫然」。[33]這幾段見於道宣著作裡的引文在自由使用的「罔冒」例中已經佔大多數,不過道
頁45
宣編著的作品,光是編入《大正藏》的,就多達一百零六卷[34]。五個小出處對篇幅超過一百卷的書籍來說,也頗能反映「罔冒」一詞罕用的程度。另一個證據是,道宣之後似乎只有元照(西元1048-1116年)一位[35]再用到這個「罔冒」。元照的年代已經是趙宋,而他的例子都出自為《〈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所作的《〈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36],所以筆者懷疑主要是受道宣的影響。
若以《大正藏》中國譯述部分的五十五大冊為範圍,「罔冒」在漢文佛典上的出處大約如此而已,顯然是個相當冷僻的語詞。至於它的意思究竟該怎樣理解,或者最起碼近人是如何詮釋它的,在現代的佛學著作裡能找到的線索十分有限。例如說,佛教專科詞書一律不收「罔冒」這個詞條,也沒有把該詞編入索引內。[37]筆者覓得的相關資料,都集中在唯識學方面的書籍。其中有一類是作者在研究《成唯識論》時提出的,像演培的《〈成唯識論〉講記》將牽涉到「罔冒」的兩句論文寫作「為罔他故」及「為網■[忙-亡+冒]他」,然後發揮為「矯設罔他」、「『為』了像漁獵一樣的『網帽他』人」[38],感覺上並沒有把「罔」或「網■[忙-亡+冒]」翻成白話[39],卻又因為「網」字的關係聯想到「漁獵」。[40]受其影響的有普行的《〈成唯識論〉研習》。該書論文雖然作「為網他故」、「為網冒他」,跟演培不同,但是從作者的譯文「為要網羅他人」、「為要像漁獵一樣,去網羅他人」[41],還是可以清楚看到《〈成唯識論〉講記》的影子。當然,普行更踏出一步,把「網(冒)」說成「網羅」。
不管演培與普行是用那些字來寫本文所討論的這個語詞,都把它看成一個概念,這點跟另兩位學者顯然有別:韋達的《成唯識論》英譯本上「為罔他故」、「為網■[忙-亡+冒]他」二句,一致地翻作“with a view to misleading and deceiving another”,[42]似乎在「罔」與「網■[忙-亡+冒]」之間畫上等號,然後將「罔(網)」跟「■[忙-亡+冒]」分開迻譯成“misleading”和“deceiving”。這個作法,韓廷傑在《〈成唯識論〉校釋》裡參考過。他把「為罔他故」與「為網■[忙-亡+冒]他」解釋成「為了把別人引入歧途
頁46
欺騙他(人)」[43],大概以「罔(網)」為「引入歧途」,以「■[忙-亡+冒]」為「欺騙」,跟韋氏如出一轍。[44]不過韓氏在他較早期的《唯識學概要》原本是認為「為罔他故」含「為了取得別人的歡心而阿諛諂媚」的意思。[45]這種理解也許淵源於太虛的《〈唯識三十論〉講要》[46],李潤生和于凌波在注釋《唯識三十頌》,措詞也都非常相似[47]。
最後提的三家說法已經屬於第二類「罔冒」詮釋材料,就是討論《成唯識論》以外的唯識經論──特別是《唯識三十頌》──的著作。此類作品裡表達的見解也不一致。除開剛介紹過的「取得別人歡心」外,主要是講「欺騙」[48],可是也有混合的想法[49]。問題在於無論以上那一個解釋,一個概念也好,兩個概念也罷,依筆者來看,都犯了望文生義的錯誤。所幸,儘管一般大部頭的中文工具書都不收錄「罔冒」,該詞卻意外地在《漢語大詞典》上出現。這部詞典提供不同方向的訊息,先對「罔冒」下定義說是指「欺騙冒充」,然後引《隋書》、《資治通鑑》和王禹偁的作品當書證[50]。特別值得讚嘆的是,它在《資治通鑑》的引文後更進一步援引胡三省的注:「罔冒,謂欺罔偽冒而求官者。以事理之所無而欺上,謂之罔;假他人之所有以飾偽,謂之冒。」
這個注很有意思,因為胡氏分開解釋「罔冒」,並從「罔」引伸出一種有、無的對立,巧妙地將「罔」字不同範疇的意義──「欺」跟「無」──湊合在一起。傳統的注釋與詞書裡,這種拆詞訓詁的情形不勝枚舉。表面上看似有道理,而事實上貼切與否,恐怕大有問題。例如把胡氏的說法硬套上漢譯釋典的「罔冒」,顯然講不通,因為它根本不含「欺罔偽冒而求官」的意思。筆者認為玄奘譯作上出現的「罔冒」很清楚原本是一個表達單一概念、由兩個同源、雙聲、單音節詞自由組合的聯綿詞罷了。理由如下:
根據上文所引文獻可以初步地瞭解「罔冒」一詞在寫卷與刊本的若干寫法。[51]撇開「■[罪-非+繯]」、「罥」這兩個音、義皆不符的訛變錯字不談,其餘雖然字形分歧,在語言方面卻完全一致。就中古音說,第一
頁47
個音節念文兩切,第二個讀莫報切[52],依照王力對隋至中唐(西元581-836年)音系的研究,可以擬構為*miuaηxmauh [53]。「罔」的微母與「冒」的明母當時尚未分,跟上古音一樣,念雙唇鼻音m,因此說,組合「罔冒」的兩個音節雙聲。[54]不僅如此,有學者主張,「网」字(即「罔」)「形、音、義皆從冖」。[55]「冒」「當是从■[冒-目]、目,■[冒-目]亦聲」[56],而「■[冒-目]」又淵源於「冖」[57],所以說「罔」、「冒」二詞同源。在隋後、晚唐前的語彙裡,這兩個源同音近的語詞可以自由組合,也就是說,除了「罔冒」的配合外,「冒罔」也有可能,而且語義一樣。[58]有意思的是,藏經裡所有「冒罔」的例子就出現在道宣的作品。[59]道宣本來就最喜歡用「罔冒」,轉來轉去,好像成了口頭禪般。[60]
至於說「罔冒」含單一個概念,而不應像「欺罔」「偽冒」、「引入歧途」「欺騙」等分開理解,總共有三個理由:一、雙音節的「罔冒」可以用單音節的「罔」來表達。《成唯識論》的「為罔冒他」、「為罔他故」是最好的說明。二、在不同的經文裡,對等於「罔冒」的詞只用單一語詞來翻譯。例如上引《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初會》第三百六十六卷經文在《第二會》第四百六十四卷有一段相等的經文說:「是菩薩摩訶薩乃至為護自命因緣,亦常不起一念忿恚惡言加報怨恨之心。假使有來欲害其命,劫奪資財,侵淩妻室,誣罔[61],罵辱,阻隔輕調,或打或刺,或割或截,及加種種不饒益事,於彼有情竟無忿恨,唯求作彼利益安樂。」[62]對等於「罔冒」的「誣罔」一詞大致指「欺騙」,漢以後就有。[63]三、「罔冒」在原典上只是一個詞。茲參安慧《〈三十唯識〉釋》「諂」('saa.thya.m)釋[64]“svado.sapracchaadanopaaya.h paravyaamohana.m”一句[65],其中paravyaamohana.m,除去para(「他人」)後所剩下來的vyaamohana.m,就是「罔冒」[66],是一個詞。它的語根√muh含「不能想事情」、「昏迷」、「感到疑惑」、「迷惑」、「弄錯」、「頭腦變混亂」等義。[67] vyaamuh雖然加上vi、ā兩個詞頭,意思沒有變[68]。因此,從muh演
頁48
變的mohana.m既然指迷惑的狀態以及讓別人搞不清楚而感到錯亂的行為[69],vyaamohana.m的語義範疇大概也不出於此。[70]
透過以上簡短的考證,可以用新的眼光來欣賞「罔冒」這個華語園圃裡曇花一現的小奇葩,或者說,可以窺出*miuaηxmauh本來面目之一斑。雖不敢妄想拙作能提供怎麼樣的服務,抑或對學界有所貢獻,但最起碼涉及釋氏經論上某小煩惱的一個語詞總算稍微獲得澄清,而解讀古代文獻的一個注意事項也應該是變得較具體些。
頁49
註釋
*本文所引《高麗藏》、《磧砂藏》、《龍藏》、《大正藏》、《敦煌寶藏》(簡稱分別為K、Q、L、T、D)、《法寶總目錄》及《〈大正藏〉索引》,皆據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版;《金藏》(簡稱J)依《中華大藏經•漢文剖分》(北京,中華書局),《大藏新纂卍續藏》(簡稱W)參臺北白馬精舍版,而《國譯一切經》則用東京大東出版社改訂發行版。藏經引用時,原則上依順標冊碼、經論編號、頁碼、欄次、行碼。
至於語文方面的參考資料,《詁林》指《〈說文解字〉詁林》(臺北,鼎文書局,民國66年3月初版),《玉篇》用臺北國字整理小組出版年月見闕的版本,《廣韻》是林尹校訂《新校正切宋本〈廣韻〉》(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65年9月),《龍龕》即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 有關慧沼的介紹,可參隆蓮寫的略傳,收於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第二輯》(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第180-182頁。
2. 諸如分別見T 39.1783、1785、1784、1786的《〈金光明經〉玄義》、《〈金光明經〉文句》、《〈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金光明經文句〉記》(參高野山大學編《〈大正藏〉索引》第二十二冊《經疏部•四•收錄典籍解題》第6-8頁)以及編入《卍續藏》的《〈金光明經〉科註》、《〈金光明經玄義〉順正記》、《〈金光明經〉照解》、《〈金光明經文句〉科》等(參小野玄妙主編《佛書解說大辭典》3.423、424、426、427)。
3. 參R. E. Emmerick, The Sutra of Golden Light: 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uvar.nabhaasottamasuutra (Oxford: The Pali Text Society,1990)第xi頁、Sangharakshita, The Eternal Legac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anonical Literature of Buddhism (London: Tharpa Publications, 1985)第249頁。二家的說法都參考Johannes Nobel的相關研究。
4. 見T 16.665.411c21-22。在曇無讖的本子裡,這個偈頌譯作「親近非聖 因生慳嫉 貧窮因緣 姦諂作惡」,見T 16.663.337a12-13。
5. 見T 39.1788.237a2-4。
6. 參《法寶總目錄》1.3.465a-b。
7. 見W 20.263.653 b12。
8. 見《玉篇》236.4。
9. 由《詁林》「■[罪-非+繯]」篆下羅列的資料看,清代的小學家對如何定位該二字,態度不一。有的把它說成俗字,帶有貶抑的意味,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邵瑛《〈說文解字〉群經正字》的「俗作『罥』」;有的提到是晚期的字形,如徐鍇《〈說文〉繫傳》「今人多作『罥』字」、戚學標《〈說文〉又考》「此字,今字書作『■[罪-非+繯]』,並省作
頁50
『罥』」;而大部分只說是或體,也就等於另外一種寫法,如王筠《〈說文〉句讀》「字或作『羂』,省作『罥』」、朱珔《〈說文〉, 借義證》「『羂』、『罥』,皆即『■[罪-非+繯]』之或體」、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又作『罥』字」、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字亦作『罥』,作『羂』」、錢坫《〈說文解字〉斠詮》「又作『罥』」。參《詁林》6.951-952。「■[罪-非+繯]」、「羂」、「罥」三形似乎都不見古文字,而《說文》僅收「■[罪-非+繯]」,所以在此以「羂」、「罥」為後起字。
10. 見《詁林》6.951。
11. 參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第三十二《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音義中引《考聲》:「以繩捕取物也。」見魏南安主編《重編〈一切經音義〉》(臺南,中華佛教百科基金會,民國86年元月初版)2.526a。
12. 如《中文大辭典》、《國語詞典》、《漢語大詞典》。當然,語詞未被詞書編輯收進去,並不稀奇:倒過來的「罥/羂 罔/網」也不見於這幾部工具書,卻為唐代的文字學家所注意。參《重編〈一切經音義〉》2.100b、325a、481b、526a。
13. 這個字形上的錯誤可能發生得相當早,但未必是中國版本的問題。日僧明一(西元728-798年)依慧沼《疏》寫了一部《〈金光明最勝王經〉註釋》。在裡面,那兩個字就寫成「罔羂」(參T 56.2197.739c18-19)。「罔羂」下、「曲順彼意」上,《註釋》有「於佛大買」四字,不知所云,而從同段文字原《疏》「妒忌稱『嫉』」,《註釋》改作「妒妄稱『嫉』」來看,明一書的版本問題恐怕不小。(《大正藏》的編輯唯一能夠參考的本子是奈良東大寺所藏的一個古寫本,參《法寶總目錄》3.41.95a。)
14. 這個統計數字見馬佩主編《玄奘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119頁(該章由程遂營執筆)。
15. 見T 6.220.887c13-18。「罔冒」二字,敦煌寫本S 4795字跡有些模糊,大約作「■[冈-ㄨ+又]■[冒-目+日]」(見D 38.21 b3-4),與《延祚藏》同(參K 34.1257.637c4)。《金藏》(大寶集寺本)、《高麗藏》都作「冈冒」(分別見J 4.1.620a2、K 3.1.552c2),《磧砂藏》、《龍藏》作「罔冐」(分別見Q 3.1.188c28、L 9.1.53 b13)。「■[冈-ㄨ+又]」與「冈」是「罔」的俗字(分別見《龍龕》329.5、《廣韻》312.8)。「■[冒-目+日]」,可洪注「莫報反」(見K 34.1257.637c4);「冐」,行均說:「莫報反。覆也。又莫北反。干也。」(見《龍龕》428.2。)都是「冒」的音、義,參《廣韻》417.8、529.9。
16. 依《大正藏》斠勘注,「斗」,舊宋本、宋本、元本作「升」,明本作「外」。《金藏》、《磧砂藏》、《龍藏》也都作「升」。
17. 依《大正藏》斠勘注,「迷」,明本作「逑」。
18. 見T 26.1536.422c21-24。「罔帽」二字,《延祚藏》、《金藏》(廣勝寺本)皆作「■[冈-ㄨ+又]
頁51
■[帽-目+日]」(分別見K 35.1257.219 b12、J 43.1031.728 b23-c3);《高麗藏》同,但在「極罔帽」、「罔帽業」二處「罔」作「■[因-大+又]」(見K 24.946.1269c1-2);《磧砂藏》作「罔帽」,並在卷末音釋中說:「罔帽,下莫報反。」(見Q 23.969-635c11-12、637 b9。)依筆者來看,「罔帽」這個詞的寫法原本跟《大般若經》一樣,作「罔冒」。「冒」之改為「帽」,是後來的發展。(這種情形,在別的經論上也有,參拙著《「頻申欠呿」略考》【收於《中華佛佛學報》第六期】第177-178頁331注。)在此沿用「罔帽」,是因為尊重現有的版本。
至於「■[因-大+又]」形,由上下文及不同的版本當然可以知道它是「■[冈-ㄨ+又]」的進一步演化。較複雜的是,本來就有一個「从囗,从又,讀若聶」的「■[因-大+又]」字(見《詁林》5.1118)。換句話說,「■[因-大+又]」是一個兼體──它兼具兩發音、意義、字形來源不同的語詞於一身。兼體的例子,另參上引拙著第169頁第238注、第171頁第265注。
19. 依《大正藏》斠勘注,「矯」,聖語藏本作「撟」。
20. 「失」,《高麗藏》作「朱」。
21. 見T 31.1585.33c8-13。依《大正藏》斠勘注,此段第一個「罔」字,《高麗藏》作「網」(《大正藏》從之),而《聖語藏》、舊宋、宋、元、明諸本作「罔」;第二個「罔」字,《高麗藏》、《聖語藏》作「網」(《大正藏》從之),舊宋、宋、元、明諸本則作「罔」;「冒」字,《聖語藏》作「■[忙-亡+冒]」,《高麗藏》作「帽」(《大正藏》從之),舊宋、宋、元、明諸本作「冒」。《延祚藏》作「■[冈-ㄨ+又]■[帽-目+日]」,並注「上文往反,下莫報反」(見K 34.1257.1052c10-11);《金藏》可惜此卷缺,無從對照(參J 30.664.740c校勘記);《高麗藏》字形原作「■[絅-口+又]■[帽-目+日]」、「■[絅-口+又]■[帽-目+日]」(見K 17.614.554c6、8;有關「■[絅-口+又]」,參拙著《〈菩薩所行方便境界遊戲神通說〉佛身光喻索隱》【收於《中華佛佛學報》第七期】第324頁139注。),《磧砂藏》與《龍藏》作「罔」、「罔冒」(分別見Q 17.633.137c18、19、L 84.1190.700 b4、5)。至於近人的斠定本,佐伯定胤監修、原於昭和十四年由性相學聖典刊行會出版的《新導〈成唯識論〉》認為舊宋、宋、元、明諸本的「罔」與「罔冒」「不可」。它主張「網」、「網帽」(加藤精神譯、勝又俊教和平井宥慶校訂的日譯《成唯識論》也是這樣用的,見《國譯一切經•印度撰述部•瑜伽部•七》第146(154)頁),並注明聖、春、祿三本「帽」作「■[忙-亡+冒]」。(見淨空民國66年在臺北倡印的佐伯著版第271頁。)韓廷傑《〈成唯識論〉校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態度不同,把「為罔他故」的「罔」保留下來,但是將「為罔冒他」的「罔冒」印成「網■[忙-亡+冒]」,且在校釋裡說明:「『網■[忙-亡+冒]』,《磧砂藏》原祚『罔冒』,《藏要》本據《述記》卷三十八改。」(分別見該書第427、433頁。)雖然沒有明說,結果其實跟《聖語藏》一樣。本文從《聖語
頁52
藏》(「罔」)、《延祚藏》(「罔冒」)及舊宋、宋、《磧砂》、元、明、《龍》諸藏(二者),統一作「罔」、「罔冒」。
22. 「諂者,謂罔他故,矯設異儀,諂曲為性,能障不諂、教誨為業。言罔他等義者,諂曲者為罔 他故,曲順時宜,矯設方便,以取他意,或藏己失,不任師友正教誨,故亦貪癡分也。」見T 44.1836.49 b15-20。(「能障不諂」的「諂」,依《大正藏》斠勘注,日本德川時代刊、大谷大學藏本作「誑」。)普泰還有一個例子見於《〈八識規矩〉補註》:「諂者,為罔他故,矯設異儀,諂曲為性;能障不諂、教誨為業。謂諂曲者,為罔 他,曲順時宜,矯設方便,以取他意,或藏已失,不任師友正教誨故,亦貪癡分。」見T 45.1865.471c8-12。
23. 「諂謂為罔冒他故,矯設異儀,險曲為性,能障不諂、教誨為業。設諂曲者,為罔冒他,曲順時宜。矯設方便,以取他意,或藏己失,不任師友正教誨故。」見T 36.1736.465 b8-11。
24. 「詐謂諂曲:罔冒於他,矯設異儀,險曲為性;或取他意,或藏己失,不任師友正教誨故。」「為獲利、譽,多懷異謀,矯現有德,罔冒於他,令他暗昧,不曉己事。」分別見T 39.1799.936 b12-14、939a26-28。
25. 「詐謂虛偽,諂謂罔冒。」見T 44.1848.395c25。
26. 《翻譯名義大集》的兩則相關引文都見於《煩惱惑業篇》。一個是在「《楞嚴》明十習:……五、詐習」下加的雙行夾注:「詐謂諂曲。罔冒於他,矯設異儀,諂曲為性。」另一個是該篇最後一項:「奢他,此云『諂曲』。罔冒他故,矯設異儀,曲順時人。」分別見T 54.2131.1150a20-21、1151c3-4。《大正藏》在「奢他」下注明“'Saa.thya”。
27. 「本非蘊識,便稱師匠;情多罔冐,每畏徵研也。」見T 52.2113.618 b7。
28. 見T 52.2133.618 b5-7。
29. 有關法琳的介紹,可參郭元興寫的略傳,收於《中國佛教•第二輯》第110-112頁。
30. 見T 52.2109.476c2-3。
31. 分別見T 50.2051.200a1-3、52.2103.161a23-24。有關彥悰的生平,參Axel Held, Der buddhistische Mönch Yen-ts'ung (557-610) und seine Übersetzungstheorie, Inaugural-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Doktorgrades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1972,第15-64頁;至於道宣,可參高觀如寫的略傳,收於《中國佛教•第二輯》第116-120頁。
32. 依《大正藏》斠勘注,「罔」,宋本作「惘」,元、明二本作「誷」。
33. 分別見T 40.1804.131c3-5、45.1895.849 b2-4、45.1896.854c10-11、52.2106.430c5-8、
頁53
50.2060.655c28-656a2。《續高僧傳》第二十五卷的部分出自宋、元、明三本,而不見於《高麗藏》,參T 50.2060.655斠勘注第36。不過《續高僧傳》早在第十五卷提過該傳的主角明琛(見T 50.2060.549c8),而且從五代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的《續高僧傳》第二十五卷音義中有「明琛」一條(見K 35.1257.610c14)來判斷,寫本的《延祚藏》也包括該傳,所以在此暫視為道宣的作品。日僧玄智於安永元年(約西元1772年)附在《釋門自鏡錄》後的資料中錄有明琛的故事,對等的引文見T 51.2083.823a8-10。
34. 見《法寶總目錄》1.4.679c。
35. 元照的簡介,可參林子青寫的略傳,收於《中國佛教•第二輯》第254-258頁。
36. 「律制堪能,須知有以。觀今罔冐,實為悲哉!」,「誡須預知,不容罔冐。」「毀祖師教,盲後學眼,罔冐之甚勿過於此!」分別見T 40.1805.192c-67、205a28、216 b16-17。
37. 查過的工具書包括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二版)、寬忍編《佛學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香港華文國際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任道斌主編《佛教文化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望月信亨主編《望月佛教大辭典》(東京,世界聖典刊行協會,昭和四十九年五月十版發行)、駒澤大學內禪學大辭典編纂所編《禪學大辭典》(大修館書店)、總合佛教大辭典編集委員會編《總合佛教大辭典》(京都,法藏館,1987年11月第一版)、中村元等編《岩波佛教辭典》(東京,岩波書店,1989年12月第一印刷)。
38. 見演培《〈成唯識論〉講記(三)》(諦觀全集•論釋四)(臺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6月天華二版)第445、446頁。
39. 這點無可厚非,日本學者翻譯玄奘的譯文也都是如此,見椎尾辨匡譯、梶芳光運校訂《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國譯一切經•印度撰述部•般若部•四》)第1218(87)頁、渡邊 雄譯、片山一良校訂《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國譯一切經•印度撰述部•毗曇部•二》)第356(70)頁、加藤精神譯、勝又俊教和平井宥慶校訂的日譯《成唯識論》(《國譯一切經•印度撰述部•瑜伽部•七》)第146(154)頁。
40. 論文的「■[忙-亡+冒]」在白話解說部分改成「帽」,也許是校對的問題,在此不贅論。
41. 見《普行法師全集之四》──《〈成唯識論〉研習》(釋普行發行,1991年四次再版)第447頁。
42. 見Wei Tat, Ch'eng Wei-shih Lun: The Doctrine of Mere Consciousness (Hong Kong: The Ch'eng Wei-shih Lun Publication Committee,1976)第438、439頁。
頁54
43. 見韓廷傑上引書第436-437頁。
44. 韓氏上引書《參考書目》第3頁中列出韋達的英譯本,可以確定是作者看過的,不過筆者也不否認韓氏的看法未必都從韋氏。例如「諂」的原文,韋達說是“Sathya”,韓延傑卻注明為“Maayaa”(見韓氏上引書第433頁)。
45. 見韓廷傑《唯識學概要》(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8月初版一刷)第191頁。
46. 參釋太虛《法相唯識學(上)》(1938年6月,商務印書館初版)第127頁:「諂是一種取媚於人的行動。」
47. 分別見李潤生導讀《唯識三十頌》(佛家經論導讀叢書第一輯)(香港,密乘佛學會、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聯合出版,1994年9月)第220頁把「諂(sathya)」的「為罔他故」譯成「為了取悅他人」,于凌波《〈唯識三十頌〉講記》(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1997年11月)第116頁在對等處,「罔」誤作「岡」,並說是「為了取得別人歡心而阿諛諂媚」。
48. 參方倫《〈唯識三十頌〉講記》(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年11月再版)第114頁以「為了欺騙他人」訓釋「為罔他故」。這種認知,在清朝的時候已經有,參吳樹虛集說、王文治撰並記《〈成唯識論〉釋並記》(臺北,大千出版社,1997年5月)下冊第440頁將「為罔他故」的「罔」解釋為「欺罔」。不過對「罔」,對書還是採取分開釋義的方式,說它指「欺罔覆冒」。
49. 參聖德《〈八識規矩頌〉講義》(花蓮,般若精舍,1987年6月初版)第105頁先肯定「罔他」是「欺騙別人」的意思,而後來又綜括地說:「為了對某一尊貴人物的逢迎巴結」。另外還有一種解釋──「為欲使他人以自己為善人故」──見於井上玄真著、白湖旡言(原作「芝峰」)譯《〈唯識論〉講話》,雖然不是華人的原著,但因為流傳頗廣(筆者看過的版本包括(一)原由武昌佛學院於民國26年5月初版、民國50年12月由海潮音雜誌社在臺北再版的本子、(二)水里,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民國78年5月版、(三)中壢,圓光寺印經會民國79年6月版(即「圓光叢書之四十八」)及(四)民國83年由「十方彿弟子印贈」、臺北世樺印刷企業有限公司承印的本子),所以也得注意。
50. 《漢語大詞典》8.1018引的這些書證是《隋書•蘇威傳》「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為官」、《資治通鑑•後晉高祖天福二年》「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宋王禹偁《搜訪唐末已來忠臣子孫詔》「人或罔冒,國有刑章,凡在守臣,副台深旨」。
51. 參綜合附表。
52. 分別見《廣韻》312.9-10、417.8-9。
頁55
53. 參王力《王力文集•第十卷•漢語語音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202-279頁。*miuaηxmauh裡的“x”和“h”只是用來區別上聲跟去聲(此方法參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5月第一版北京第三次印刷】第33頁),因為具體的音值不得而知。
54. 當然,它主要的母音也相同,都是*a。
55. 見齊沖天《聲韻語源字典》(重慶,重慶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165頁。
56. 見《詁林》6.933引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
57. 見《詁林》6.913引章炳麟《文始》。
58. 這種「反轉組合」,中文的例子還不少,參徐振邦《聯綿詞概論》(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142-148頁。不過徐著並沒有提「罔冒」。
59. 即《釋門歸敬儀》「道貴清通,義非壅結,仍須識分,以自揣摩,無容冒罔,自謂超挺」(見T 45.1896.858 22-24)、《續高僧傳》「乃見談述高邃, 罔天地;返顧小道,狀等遊塵」、「非時之食對俗而噉,公違法律,現罄滅緣,冒罔聖凡,一至於此」、「卿等結聚作何物?在依何經誥?不有冒罔後生乎」(分別見T 50.2060.508a16-17、624a17-19、641 b24-25)、《集古今佛道論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玄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臥棘」、「劉、李違師背教,妄作冒罔凡聖」、「唐梵音義確爾難乖,豈得浪翻,冐罔天聽」(分別見T 52.2104.36.a16-18、381a6-7、387a9)。其中《集古今佛道論衡》第二個例子特別有意思,因為據《大正藏》的斠勘注,舊宋、宋、元、明等本在此作「罔冒」。
60. 《續高僧傳》另有一個前後用「罔」、「冒」的例子:「屬周武之時,道士張賓譎詐罔上,冒增榮寵。」見T 50.2060.626 b20-21。
61. 「罔」,據《大正藏》的斠勘注,《高麗藏》作「誷」。茲從宋、元、明等本。
62. 見T 6.220.345 b29-c5。
63. 參《漢書•王莽傳上》:「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說自此始矣。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太厚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這也可以參考跟上文所引《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偽斗偽秤,偽函偽語,於他罔帽」類似的、見於《佛名經》系典籍的「輕秤小斗,減割尺寸,盜竊分銖,欺罔圭合」。見T 14.441.212c11-12、273a2-3、447.380 b19-20。(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本,「斗」作「升」,參T 14.441.311 b1。)
64. 由此來看,韓廷傑認為唯識講的煩惱中「諂」指“Maayaa”是有問題的。
頁56
65. 參霍韜晦《安慧〈三十唯識釋〉原典譯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專刊【1】)(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第182頁。霍書原作“paravyaamoohana.m”,是不可能的,因為梵語的“o”寫成文字沒有長短的差別,而且霍著《附錄二:梵漢語彙對照》第245頁也僅作“paravyaamohana.m”。
66. 霍著第88頁把svado.sapracchaadanopaaya.h paravyaamohana.m譯成「隱蔽自己的過失以為方便者,(目的)即是惑亂他人」。徐梵澄《安慧〈三十唯識〉疏釋》(北京,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1990年6月出版)則作「方便隱藏己過者,即冒罔他」。
67. 參Monier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Tokyo: Meicho Fukyukai Co., Ltd., 1986 reprint)第824c-825a頁。
68. 同上,第1038b頁。
69. 同上,第836a頁。
70. 這也可以參考Dharmaskandha的moha.m sa.mmoha.m pramoho(見Siglinde Dietz, Fragmente des Dharmaskandha: Ein Abhidharma-Text in Sanskrit aus Gilgit [An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Dritte Folge, Nr. 142][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4]第25頁;對等的漢譯「癡、等癡、極癡」見T 26.1537.505c26)。《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的「罔帽、極罔帽、遍罔帽」可能就來自類似*mohana.m sa.m(pra)mohana.m pramohana.m的組合。
附錄:字形演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