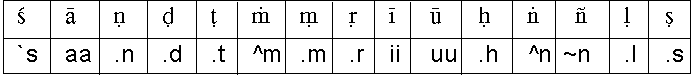
中國佛教譯經史研究餘瀋之二
曹仕邦
貝葉
第八期
頁8-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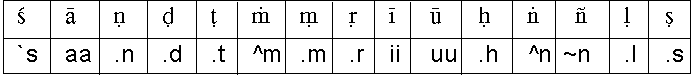
頁8
——前期貝葉,仕邦曾以同一題目寫了一篇雜考,並於篇末稱:「將來有暇,還會繼續撰寫」,今謹再提出如下數則:
五、譯場嚴格要求參譯人員通習梵文的時代
一九六三年仕邦發表「論中國佛教譯場之譯經方式與程序」一文(刊新亞學報五卷二期),考知自漢末以迄北宋初期前後近九百年間「譯場」集體翻譯方式的制度演變和分工效能,發現古代翻譯有一特殊現象,就是參加譯場的成員並無嚴格的語文要求,不通梵文的固然可以,不懂中文的也未嘗不可,只要具有合乎翻譯需要的一技之長,便都被歡迎參加這功德無量的文化事業。原因是除非「主譯」是通習梵文的華人或曉講漢語的西僧外,差不多譯場中經常設置一位稱為「傳語」的人員負責溝通中印語文的工作。
撰寫該論文的時候,由於未能接觸到保存於「宋藏遺珍」中的譯經史料;而不知道譯場發展至宋代,參譯人員是必須先受梵文訓練的,今謹將此事補論如下:
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三略云: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十月,譯成經五卷,詔以其經入藏頒行。(主譯)天息災因奏曰:臣等竊見教法東流,歷朝翻譯宣傳佛話,首在梵僧,其如天竺中華,方域懸阻,或遇梵僧有闕,則慮翻譯復停。臣等欲乞下兩街僧司選諸寺院童子五十人,就譯經院先令攻習梵文,後令精究梵義,所貴成就梵學,繼續翻宜。上可之,乃詔殿頭高品王文壽於左右街僧司,集京城出家童子五百人以選之,得惟淨等五十人。是月,左街僧錄神曜引惟淨等於崇政殿,上令各誦所習梵文,仍諭以勵力勤習,用副精選,即日竝送譯經院受學。
天息災之所以考慮到後繼無人;提出精選出家童子自幼予以梵文訓練以作接班人的原因,可以分兩方面來講。第一,宋代譯經事業完全出於帝王獨力支撐,並不為佛教界普遍支持。大中祥符法寶錄同卷略云:
左街僧錄神曜及諸義學僧咸以為譯場久廢,傳譯至難。時義學僧執所譯經。天息災等持其梵本,華梵對譯,義理昭然。由是神曜等及義學僧百人列表上言稱今之所翻,與古譯合。
佛祖統紀卷四十三法運通塞志略云:
時左街僧錄神曜等言,譯場久廢,傳譯至難。天息災等即持梵文,先翻梵義,以華文証之,曜眾乃服。
兩條史料所記是同一件事,從上述的記載,知道興立譯場之初,連政府委任以管理僧尼的僧錄神曜也對翻譯能否實行感到懷疑,結果耍天息災等與一群反對者分別持梵、華經本當場相對解釋以為定奪,纔博得神曜等百多位義學僧的信服。由這件事,已知訓練接班人的重要了。
其次,自東晉以迄隋唐,是中國佛教最發達的黃金時代,那時翻譯事業所以能持續不衰,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不斷有印度或西域的高僧和居士東來弘法,故隨時可在中國就地找到譯埸所需的人才。而到了宋代,天竺佛教經已衰弱,西僧來華者漸稀(參
頁9
陳觀勝先生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一書頁三九九——四○○),故天息災纔有中印「方域懸阻,或遇梵僧有闕」的考慮。因為天息災本身也是當時少數來華的梵僧之一(見補續高僧傳、新續高僧傳卷一本傳,參冉雲華先生 Buddhist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Sung China 一文,刊 History of Religions 六卷一、二期)。
天息災等的考慮是有遠見的,由他們的建議而被選受訓的惟淨(前引大中祥符法寶錄特別標示他的名字)後來果然堪當大任。景祐新修法寶錄卷九略云:
(宋仁宗)天聖五年(一○二七)十二月起,譯論一部十八卷巷,至八年(一○三○)四月譯成全部,三藏沙門惟淨、法護譯,沙門文一筆受,沙門簡長綴文,沙門法凝、禪定、令操、善慈、惠真、遇榮、鑒玉、志純、鑒深、清才、慧濤、潛政証義,樞密副使刑部侍郎夏竦潤文,入內內侍省高品陳文一監譯。
天聖五年去太平興國八年凡四十五年,而天息災等訓練出來的華僧惟淨經已充當主譯了。同時由於參譯人選都受過梵文的訓練,故宋代譯場一直未設置「傳語」之員。
六、三僧傳對譯經西僧名字標目的演變
自漢末至唐,是佛教傳入中國以至發展達最高峰的時期,印度和西域不斷有許多僧人前來弘法,而這些西僧中之曾在中國翻譯佛經的,其名字在梁、續宋三高僧傳的目錄中底標示方式頗不同,大抵高僧傳標目用其名的音譯,如卷二「晉長安鳩摩羅什傳」,而傳文略云: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
同書同卷「晉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傳」,而傳文略云: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迦維羅衛人。
「鳩摩羅什」與「佛馱跋陀羅」是音譯,傳文中的「童壽」與「覺賢」是義譯。續高僧傳則趨近略譯,如卷三「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而傳文略云:
波羅頗迦羅多羅,此言作明知識,或一云波頗。
同書卷四「唐京師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而傳文略云:
那提三藏,此言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烏伐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
「波頗」是「波羅頗迦羅多羅」的略譯,「那提」則因「布如烏伐邪」音煩致訛略而成的音譯,「明知識」與「福生」當然是義譯。宋高僧傳則標目多採用義譯,如卷一「唐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傳」,而傳文略云: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
同書卷三「唐洛京天竺寺寶思惟傳」,而傳文略云:
釋阿你真那,華言寶思惟,北印度迦濕密羅國人。
「金剛智」與「寶思惟」是梵音「跋日羅菩提」與「阿你真那」的義譯,方式與高僧傳根本顛倒。茲為方便了解,謹將三僧傳譯經篇中全部西僧名字的目錄標目、華梵譯名及國籍為製一表,並依馮承鈞先生歷代求法翻經錄補入馮氏為西僧名字還原的梵音(所附數目字,乃馮氏原書的編號),羅列如下:
頁10
|
||||||||||||||||||||||||||||||||||||||||||||||||||||||||||||||||||||||||||||||||||||||||||||||||||||||||||||||||||||||||||||||||||||||||||||||||||||||||||||||||||||||||||||||||||||||||||||||||||||||||||||||
|
高僧傳
續高僧傳
宋高僧傳 |
|
頁11
|
|||||||||||||||||||||||||||||||||||||||||||||||||||||||||||||||||||||||||||||||||||||||||||
|
宋高僧傳 |
|
從上表,知道高僧傳以梵名標目以至一百八十度大轉變而為宋高僧傳的多採華文義譯名字標目,其界綫在於續高僧傳「波頗」、「那提」兩僧名之以梵音略譯標目,兩僧是隋唐時人(見本傳),則其轉變也略似譯經方式的轉變,以隋為界綫(見拙作論中國佛教譯場之譯經方式與程序一文的「結語」,刊新亞學報五卷二期)。
這一轉變如何產生的呢?仕邦以為魏晉六朝是佛法的輸入期,翻譯佛經視為第一要務,故高僧傳以譯經篇冠首,而譯經要靠西僧主持,因此標示其梵名音譯以示非華僧,使人望而生敬。那時甚至華僧也有以梵名行世的,如高僧傳卷三宋黃龍釋曇無竭傳略云: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遠適西方,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於廣州。
曇無竭的姓氏、籍貫都純粹是華人,其使用梵名可解釋謂曾去西方留學,故取此名以便在域外酬對,但同書卷十晉洛陽婁至山訶羅竭傳略云:
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晉武帝太康九年(二八八)暫至洛陽,晉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乃西入止婁至山,至元康八年(二九八)端坐從化。
像訶羅竭,他的籍貫是樊陽,自出家至圓寂未離中國,要是他屬於域外人而生於中國者如康僧會、竺叔蘭之流。高僧傳必為標示(見卷一康僧會傳及卷四朱士行傳),而今竭公傳中沒有說他是域外人,可見是華僧採用梵名。此無他,況之近人好取洋名如「彼德」、「安妮」之類,即悟其故。
然而梵名音譯讀來未免拗口,尤其隋唐以後力追原音正譯,如玄奘撰大唐西域記卷二序說稱:
詳夫天竺之稱,舊云身毒,或曰豎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
即其例。由於求聲調之正,則音譯更為拗口,如表中之「勿提提
頁12
羼魚」、 「阿目佉跋折羅」、「戍婆揭羅僧訶」等不特艱於上口,而且叫人難生敬意(如「勿提提羼魚」很可能被戲稱為「亞魚」),於是首先有續傳的「略譯」方式出現,到了宋傳,索性多使用義譯,如上引三人之為「蓮華精進」、「不空」、「善無畏」、不特能勾起讀者對佛法的敬意,並且名字與華僧相若,易生親切感。宋高僧傳的轉變,也多少屬於佛教走向「中國化」的表現之一。到了宋以後,僧史對西僧的名字,如見於明高僧傳、補續高僧傳、新續高僧傳等譯經篇中的域外沙門,多以義譯如「天息災」、 「法天」、「施護」等標目。
七、評季羨林「記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發現」
近代的佛學研究有一股歪風,某些人得緣從歐美或日本學到一些梵語梵文的知識後,動輒據殘存的梵文佛經原本來批評中國古代所譯佛經的不當,如「不忠於原文」啦,「漏譯某些部份」啦,「譯文中某些字眼表達得不夠力量」啦,諸如此類,藉以炫耀自己學來的梵文知識,好像魏晉譯場中的三千助手或隋唐翻經的諸大德底全部心力都比不上他或她所學到的丁點梵文(其實可能連發者都不準確),而不思當時翻譯何以有此取捨。近讀「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一書(香港龍門書店印行),中有季羨林撰「記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發現」一文,就是據梵文知識輕評古譯的例子。
季氏文中說由於這部律典的原文被發現後,知道唐代義淨三藏譯此律時僅限於散文部份忠於原本,而韻文部份則不然,並舉了如下的例子(在該書頁一七九──八○):
中譯本第二首(梵詩)是:
善調伏諸根,如法淨身意,廣大功德海,我今略讚歎。
梵文是:Pranidhaya Mana.h
Sahendrlyair Vidhivad Vaak Ca
Saarlram eva Ca l
Gunabhuuta Mahaagunodadhes tava
Vaksyaami Gunaikade'sataam ll
我們的譯文是:
你如法調伏了意,言,身,連同其他諸根,是功德的人呵!我讚歎你的廣大功德海的一部份功德。
中譯本的第三首是:
論義中第一,調伏無過失,能知第一義,擊論不能動。
梵文是:Paramapravaro Sivadinaam Anavadyah
Susamahitendriyah l
Paramarthavid Aprakampitah Prayataih
Sarvapara Pravaadibhih ll
我們的譯文是:
你在論義者中是第一,你沒有過失,你的諸根都約束好了,你堅持第一義,不為其他提出來的議論所動。
中譯本第四首是:
明行得圓滿,善達諸禁戒,勝定如山王,力等那羅延。
梵文是:Caranam Susamaaptam eva te
Susamaptavrata Saadhtavratah; l
balavaams Ca samadhiravyas tave
Naaraayanasaila rajavat ll
我們的譯文是:
你的明行圓滿了,你的禁戒都已達到,都已完成,你的三昧是那羅延山王一般地有力而不能動搖。
到這裏中譯本的話就完了,接著是「如是為首,以五百頌讚歎世尊已。」但梵文本的詩一直到四十首纔完。但為什麼中譯本比梵文中少這樣多呢?西藏本也比中譯本多。這使我們有理由推測,義淨大概把那些詩刪掉了,沒有譯。所謂義淨譯經對原文忠實也只限於散文部份,韻文部份就不然。
頁13
讀了季氏的偉論,不禁掩卷三歎!且不問季氏對中國譯經史已懂多少,就從嚴又陵先生所提倡的翻譯「信、達、雅」三原則(也是近代翻譯界所服膺的三原則)而言。梵文詩是韻文,義淨以詩體譯之,這是「信」!季氏之所譯則僅求表意,連「新詩」也談不上!至於「雅」,參觀兩者所譯,一望而知誰比較「雅」!
談到「達」,義淨為了「信」而譯成詩體,唐代流行五言七言詩,不流行魏晉時的長短句,故淨公以五言譯出,由於規格所限,每句都只能用五個字,則譯成現在的樣子,已屬難能。仕邦不懂梵文,但試比較淨譯與季譯(季氏自以為正確的譯法),便知義淨對「達」用了多少功夫!
據季民所譯第二首,好像義淨的「如法淨身意」句中漏譯了「言」字;且「淨」字多餘,又「廣大功德海,我今略讚歎」漏了「是功德的人啊」等字樣。然而中國成語有「言為心聲」、「意在言外」等,言語不過心意的表達,既然「如法調伏」了「身」和「意」及「諸根」,則「言」已包括於「意」中,為了格律,這不算漏譯。又佛家約束「六根」而使「六塵」不入謂之「六根清淨」,故「淨」字是為了強調「調伏」二字;並且顧及協律而使用的。再者,五百頌都為了「讚歎世尊」,義淨譯本中早有交代,則「是功德的人啊」何必再提!此外,「功德海」的「海」字是形容詞,「我今略讚歎」當然指佛陀如海般廣大的功德的一部份功德,何必如季譯的囉唆!
季氏譯的第三首看來與淨譯無甚出入,「調伏」據前引第二首是指對「諸根」的約束,則「調伏無過失」已包括季譯「你沒有過失,你的諸根都約束好了」的兩句。又「擊論不能動」,「擊論」指「其他提出來的議論」,因為它們是用來對付第一義的,可謂一種「攻擊」,既然「擊論不能動」佛陀的「第一義」,已暗示佛陀對第一義的堅持」。淨譯使用「擊論」二字,較之季譯同句來得生動和有力!
據季氏譯的第四首,好像義淨漏譯了重要的「三昧」一詞,又好像把「那羅延山王」分成兩種事物,更好像未交代「禁戒」都已「完成」。實則,華文中「完」與「善」兩字經常連用,以「善」來代替「完成」,在訓詁上非講不通,則「善達諸禁戒」已具備「你的禁戒都已達到,都已完成」的意思了。
復次,「勝定如山王,力等那羅延」兩句據季譯應是「那羅延山王一般地有力而不能動搖」,蓋讚美佛陀的「三昧」底形容語詞,似乎淨譯將「那羅延」與「山王」硬分開了。問題是「那羅延山王」據季氏文中所舉梵文乃:Narayana Sailarayavat 一字,而其中:Narayana 即「那羅延」,據南宋釋法雲所集的翻譯名義集一書卷二鬼神篇的「那羅延」條稱:
翻(為)鈎鎖力士,或翻(為)堅固。
此外,中國佛教月刊社印行的「漢英佛學大辭典」(據倫敦出版,由 Soothill and Hodous 二氏主編的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一書影印)頁二四八「那羅條」亦解釋「那羅延為 firm and stable 和 Nero of divine power (參丁福保佛學大辭典頁一二一八──一二一九的「那羅延條」)。又據上引大辭典頁三九六「勢」條及法雲書卷三眾生篇「勢羅」條,知:Saila 即「山」。又 Rajavat 雖上引大辭典所無但 Raja 即「王」,則見其書頁一六三。至於「山王」,據丁福保佛學大辭典頁四五○山王條稱:
謂山之最高者,在諸山中為王也。無量壽經下曰:智慧如下海,三昧如山王。法華經法師功德品曰:彌樓山,摩訶彌樓山等諸山王(參漢英佛學大辭典頁一○二「山王」條)。
仕邦不知道印度古代是否有一種叫作「那羅延山王」的最高峰,丁氏大辭典所舉既無此名,而據磧砂藏第一三○冊鳳,頻伽藏盈帙一冊及大正藏卷九法華涅槃部的妙法蓮華經法師功德品(前二者在卷六,後一者在卷八),其「摩訶彌樓山等諸山」句下都無「王」字,未知丁氏何所據。抑有進者,翻譯名義集卷三眾生篇中言及印度諸大山(包括傳說的與實在的一,都未提及此一山名,而法雲著書於宋高宗紹興十三年(見其書卷首自序),去北宋
頁14
譯經時代猶近,既然法雲不知有此山名,故管見以為「那羅延山王」大抵乃印度佛教界慣常用以形容「堅定有力」的譬喻詞(上引丁氏大辭典,不是提到無量壽經說「三昧如山王」嗎?而季譯的「那羅延山王」正好也是形容「三昧」的),並非實際地名,蓋「那羅延」既指「力士」,而「山王」屬「山之最高者」,應當是「不可動搖」。若仕邦的推測為合,則淨譯將「那羅延」與「山王」拆開,分別使用,未算不通,並能使譯文的形容更見有力,且顧到五言詩的格調,因為這究竟是譬喻而非專有名詞。
再者,淨譯沒有提到「三昧」,似乎是一大過失,但據翻譯名義集卷四論開八聚略云:
三昧,此云調直定,又云正定。遠法師云: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
「三昧」的原義既為「禪定」的「定」,則淨譯何嘗沒有翻譯「三昧」一詞,不過採其義譯而已。又漢英佛學大辟典頁五七三「三昧(地)」條略云:The there Samadhis on there Subjects 三三摩度(地);三定(中略) there are two forms of such Meditation (下略)。
是「三昧」乃一種「禪定」,其原文為 Samadhis ,跟季氏所舉梵文中 Samadhiravyayas一詞相關。則淨公譯「三昧」為「定」,更証明完全正確!然而淨譯以「勝定如山王」一句概括了「禪定」的「定」與「不能動搖」的「定」,犯上淆混的毛病,大抵淨公以「那羅延山王一般地有力而不能動搖」是形容佛陀的禪定力,為了顧及詩的規格,故以「勝定」二字來標示「三昧」,而利用「山王」來暗示「不能動搖」。
問題是季羨林何以使用非學佛之人不能曉的「三昧」一詞,而不採一般人都能了解的「禪定」來翻譯此句?難道有意欺別人不習以掩義淨的正譯?若然,手段可謂卑鄙!
最後,季氏據梵本原有四十首詩,而義淨僅譯了三首,認為這也是淨譯對原文不忠的証據。不錯,若必「畫地為牢」式圈定了「是否按照原來樣子」作定奪,而當日義淨所據梵本也有這四十首詩,則淨公刪而不譯,當然是不忠!但另一可能卻是:當日傳來的梵本僅有這三首詩,與季氏所見本不同(故季氏對此也僅作推測而不敢肯定)。就算淨公真個把三十多首詩都刪去不譯,也有他的理由,因為譯經的主要目標在於弘揚佛法,原本讚美世尊的話若太多,等於歌功頌德的口號喊的大多,反易使人產生反感,對弘法事業是有害的,故即使曾有刪詩之舉,也是在「弘法利生」的大前題下犧牲「忠於原著」的小節而已!
然而季氏這篇據梵文原本來批評義淨舊譯的論文,也是有它一定貢獻的,要不是標舉梵文並譯出其義,何能証明淨譯是「擊論不能動」的譯作!